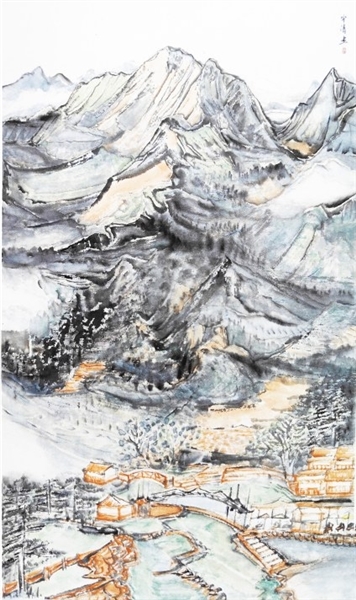
韩富贵更不服:“耍埋汰谁能耍过你?你咋当的饲养员,谁还不知道?”谁都知道饲养员是队里挣工分最多的,但棒劳力当不上,郑万山当年从山坡上滚下来,一瘸一拐了半年多,就当上了。一提这话茬儿,郑万山鼻子沟都泛白,眼看着汗就要冒出来。韩富贵身边站着的老铁匠,这时赶紧拍了拍韩富贵肩膀,说道:“富贵呀,说铃铛,你不是想要铃铛?”韩富贵从不跟老铁匠斗嘴儿,又说回了铃铛:“我不要,谁也不要。我一要,全都想要。都他妈的——眼皮子浅、腚沟子深!”
院儿里又是一片七吵八嚷。
一个鼓眼珠子的老头,嘴巴松开烟袋锅,像是鼻子里哼了一声,对老铁匠低声说道:“他们几个,争啥争呢?要那么论,这铃铛最早是人老阚家的。”这老头姓庞,脖子上有个瘿袋。
“老庞头,你个老粗脖儿,”韩富贵不光嗓门儿大,耳朵也机敏,冲着老庞头嚷,“分老阚家浮财那前儿你多大?三四十有吧?我才十来岁,咋还没我有记性?那头青骡子不是分给我家了?”老阚家是当年第一大乡绅,家财万贯,整个东山都是他家的。斗阚大地主最积极的就是韩富贵他爹,分财产分得最多的,也是韩富贵他爹。
老庞头被损得灰头土脸,举着烟袋锅,不敢吭气儿了。这人平时话挺少,老两口儿拉扯个外孙子,名叫庞大海,日子紧巴巴。倒是郑万山,心也不服嘴也不服,又戗戗道:“韩富贵,你嗓门儿大,你倒是问问铃铛那物件儿,它想跟谁?”
院儿里舞马玄天,正在难分难解,村小学左校长走了过来。迈着四方步,不紧不慢。
左校长细眉细眼,架副眼镜。走路挺胸抬头,颇有几分文气。怪就怪在常年只戴一只套袖,有时藏蓝,有时墨绿,弄得总有一只胳膊失真。那天他左胳膊一半浅灰(衬衫是灰的)一半藏蓝,抬起来扶了扶眼镜,站住了。
“乡里乡亲的,大家不要吵嘛!”
“左校长,来得正好,您给评评理,韩富贵是不耍埋汰?”
左校长温和地笑了笑,“多大个事儿,说来听听。”
“嘻,屁大个事儿。”郑万山儿子叫郑四方,正在村小念书,数他最知道见啥人说啥话。“你个孬种!左校长,斗大个事儿。”韩富贵脾气直,总说自己下辈子再起名就叫韩正义。
“说说看,松花她爸。”韩富贵大闺女叫韩松花,也在村小念书。韩富贵跟谁都敢耍驴,就跟两个人不耍:一个左校长,一个老铁匠。要不是这位左校长,韩松花怕是连学都没的上。每学年那五块钱学费,在老韩家是天大个数。眼瞅着别人都上学了,韩松花跪在地上,央求韩富贵让她也去上学。韩富贵差点把牙咬碎,骂了半晌,出门去找了左校长。见了面儿先骂自己混蛋,明明养不起,还一个接一个,连生了三个。生完又塞不回去,连五保户都没资格申请。两口子像俩废人,一丁点来钱道儿也没有,每天太阳一出来就愁,月亮挂头顶时继续愁。左校长知道他家啥样儿,二话没说就去大队开证明,又是申请又是上报,韩松花的学费一分也不用交了。韩富贵一琢磨,老二老三离上学也不远了,就把那两个减免学费的事,提前对左校长千恩万谢了一番。左校长最怕村里哪个娃没学上,韩富贵等于用自己的娃戳了左校长的软肋。校长答应了——万一申请不下来,那俩娃学费,他从工资里掏。
韩富贵围着左校长转了五六圈,抢铃铛的事才算说清楚,正要继续转,有人受不了了。“韩富贵,你让叫驴附体啦?那是左校长,你当磨盘啦?”有人哄笑,有人加纲,说叫驴回来了,给自己转迷糊了。韩富贵借这话表现出一副勃然大怒的样儿,抓起拴着铃铛的绳套,二话不说,自脑瓜顶一套,叮叮当当,把自个儿拴住了。
“松花她爸,你这气性,还真是挺大。”左校长到底有文化,憋住了,仅带一丝微笑,别人没这功夫。一时间,老榆树的荫盖里没了好动静,大笑声连成片,听着像野鹅狂叫。韩富贵丢了面子,却捞到了实惠,象征性地又喊了两嗓子,两条腿一高一低,把自己拐回家去了。
这位左校长不是别人,正是我爸。他回家学抢铃铛那件事时,我七岁,读村小一年级,跟韩松花、郑四方还有老庞头的外孙庞大海一个班。我爸那天说完那事儿,加了句总结:“有人的地方就有矛盾,有矛盾就需要有解决矛盾的人。”我觉得我爸有吹嘘他自个儿的成分,我妈说那是知识分子的通病。我想,既然是通病,我爸肯定也得上了。不过我还是抱了一线希望,问我妈:“所有通病都有疫苗吗?”我妈以会计对待账本的认真态度对我说:“哪能呢?我听说外国有个什么滋病就没疫苗!”我对我妈的回答不太满意,又说不出不满意在哪儿,于是又问:“妈,你算知识分子吗?”
我妈是村供销社卖货的,主要负责入口的东西,酱油醋、青方红方,尤其是来自海边的一种小咸鱼,最紧俏。那年头,为了买青红方时能多得几滴汤汁,我妈就被拥戴为全韩屯最受欢迎的人。不管春夏秋冬、阴晴雨雪,谁见到她都一扫脸上的阴霾和惆怅、劳累和疲惫,大老远就欢声笑语、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地招呼:“彩霞!小王!王彩霞!”重点是:我妈有个理论,只要挣工资、吃卡片儿的,几乎都是知识分子。她就是到点儿就开支的。
面对我的询问,我妈态度越发认真,皱了皱眉头,使劲儿思索一下,对我说:“算,我觉得我算。”
我心想,看来我妈说的那个知识分子的通病,是真的。没有疫苗也是真的。她和我爸都得了。
可我妈好像早已忘了那话。因为接下来她又一次郑重地对我说:“天伦,只要挣工资、吃卡片儿的,准准的都错不了,你以后也得当个知识分子。”
这话一直陪伴我,隔三岔五萦绕耳畔。直到高三那一年。 (选载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