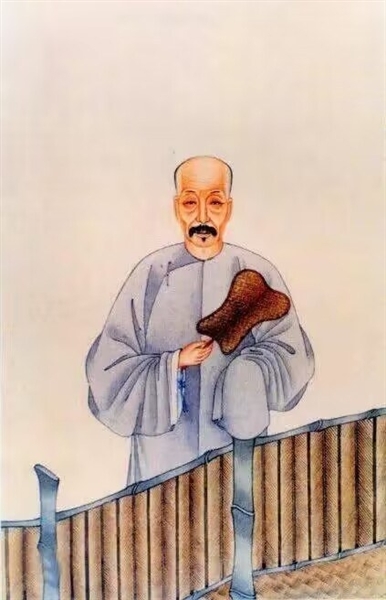
在鸦片战争前后,岭南地区以学海堂为中心的不少学者一直以开放的心态积极了解并介绍西方文化,曾任学海堂学长的名儒梁廷枏(1796-1861,字章冉,号藤花亭主人,广东顺德人,见图)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海国四说》
魏源的《海国图志》一直被誉为晚清介绍西方世界的扛鼎之作。梁廷枏则撰有《海国四说》,付梓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海国四说》由四个部分组成,分别是《耶稣教难入中国说》《合省国说》《兰仑偶说》与《粤道贡国说》。全书中单列的国家只有两个,《合省国说》讲的是美国,而《兰仑偶说》讲的是英国,从顺序来看,美国的地位还在英国之上。
站在今天读者的角度,对美国的重视似乎是顺理成章之事,可是在19世纪中叶,美国还尚未成为世界第一强国,而清朝所刚刚遭受的惨败则拜英国所赐,与美国的铁拳并无关系。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梁廷枏居然把美、英列为两个最重要的国家,并且把美国放在英国前面,可谓独具慧眼。《海国图志》对美国的介绍虽然篇幅宏大,但是从时间上来说反而在《海国四说》之后,梁廷枏对美国的看法应该说具有一定的原创性,《合省国说》也可以被视为中国第一部关于美国的通志。
发现米利坚
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梁廷枏曾应两广总督卢坤之邀,担任广东海防书局总纂一职,专门负责搜集整理与中国有贸易往来的各国信息,编纂了《广东海防汇览》四十二卷。由于清朝广东在对外经济交流中的独特地位,身处近水楼台的梁廷枏对世界各国的了解在当时可以说非常深入。他目光如炬地发现,美国与包括清朝在内的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有着一个本质的不同:世界上所有的其他国家“莫不奉一君主”,可是美国却恰恰相反,“未有统领,先有国法”。
“法也者,民心之公也”,民心正是自古以来儒者们所津津乐道的。既然法治就是民治,那么它距离中国的传统也就并不遥远。梁廷枏用中国人最熟悉的概念解读了美国与清朝在政体上的异同。他认为美国的国法之公让结党营私之徒没有了机会,杜绝了暴君统治的可能性。可以说,梁廷枏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就有了一种模糊的观念:中国不改变帝制就无法真正强大。
之所以说是模糊,是因为梁廷枏并不能真的想象一个没有了帝王的中国。他认为这样的体制难以复制,“必米利坚之地、之时、之人而后可”。
一条可行之路
梁廷枏在无法废除帝制的情况下指出了一条明路——通商贸易。一方面,“西国之风气,唯利是图”,因而重要的是满足他们的通商欲望;另一方面,华盛顿通过奋战逼迫英国签了城下之盟,维护了美国人民的利益,使原本是英国属地的美国摆脱了英国的统治,这可谓给经历了战败的清朝树立了一个榜样。
梁廷枏用自己的行为告诉世人如何和英国人对抗。道光二十九年(1849),英国人向两广总督提出要求进入广州城。官府不敢抗拒,也不想答应,就把锅甩给了百姓,希望动用民间力量让英国人知难而退。官府下令让粤秀、越华、羊城三大书院引导民众自卫,可是毫无成效。此时的梁廷枏振臂一呼,联合谭莹等地方大绅,亲自号召民众团结一致抵抗英国人进入广州,数日内就组成了数万团勇,在珠江沿岸严阵以待。梁廷枏亲赴英国领事馆,慷慨激昂地表达了广州官民誓死拒英人入城的决心,逼迫英国人最终收回成命。
这样的一条开放之路在当时并未得到认同。一直被誉为晚清先进思想代表的龚自珍就旗帜鲜明地反对贸易而重视农耕,梁廷枏知音难觅。
从天下到国家
与魏源在《海国图志》序言中直接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不同,梁廷枏并不认为国家之间必然是一种“制”与“被制”的关系。魏源把制服世界各国比作清朝对准格尔的征服,提出“何患攘剔之无期”。这样的态度说到底还是默认清朝为天下的中心,把其他国家视作低人一等的存在,认为清朝总有一天会把它们消灭干净。
相反,梁廷枏从未有这样的“雄心”,他反复强调的是如何在怀柔的前提下既能抵御外侮,又能贸易流通,从而找到一条复兴之路。梁廷枏把国与国之间相处的核心归于“利”,而交相利的手段则是贸易。因此,他把外国视为商业贸易的伙伴,完全摒弃了对外国“夷”的称谓,从这一点来说,他已经具有了朴素的现代国家观念。他比梁启超早半个多世纪就意识到了国家与国家之间应当具有的平等关系,更是认清楚了清朝不是天下中心的事实——因此他的《合省国说》与其说是对美国的介绍,不如说是帮助清朝在新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尽管这样的定位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有些难以接受。 (摘自《文史天地》2023年第12期 董铁柱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