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8年春,钱三强(右)回国前夕在巴黎与约里奥-居里夫妇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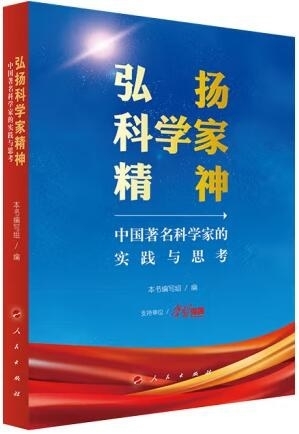
(摘自本书编写组编《弘扬科学家精神:中国著名科学家的实践与思考》,人民出版社2024年1月出版)
“法语程度还不错嘛”
1936年夏天,我告别清华园,走上了社会。我毕业后,有两个可供选择的前途:一个是到南京军工署研究机构工作,另一个是到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去。我选择了后者。所长严济慈先生分配我从事分子光谱方面的研究,并兼管研究所的图书室。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严先生找我去谈话。他取来一本法文科技书,让我念给他听听。他听了一会儿,说:“法语程度还不错嘛!”之后,才告诉我为什么要考察我的法文,原来是想让我去考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到法国留学的公费生。当时有三个留法名额,其中之一是到居里实验室去学习镭学。严先生希望我能去学习这种当时最前沿的学科。在他的支持和鼓励下,我考上了。1937年夏天,我就进入了世界闻名的居里实验室。
居里夫人发现了镭,是放射化学和原子核物理学的奠基人。居里夫人即使在成名之后,很长时间内也还没有一个真正的实验室。直到她的晚年,法国政府才拨款在巴黎大学建造了一个镭学研究所,由她主持研究工作。居里实验室就是镭学研究所的组成部分。居里夫人逝世后,居里夫人的长女伊莱娜和她的丈夫弗莱德里克·约里奥继承了前一辈的事业。
样样都得学会才行
20世纪30年代的居里实验室,保持了世界上最先进最重要的原子核科学研究基地之一的地位。这并不是依靠了居里夫人的名声,而主要是由于约里奥-居里夫妇的一系列杰出的工作。我能够在弗莱德里克·约里奥和伊莱娜·居里夫妇领导下做研究工作,实在是我的幸运。
我到了巴黎之后,跟着约里奥先生做博士论文实验设备的准备工作。在实验室,我尽量多干具体的工作,除了自己的论文工作以外,一有机会就帮别人干活,目的是想多学一点实际本领。我找到伊莱娜夫人,提出希望参加一点放射化学的实验。她把我介绍给化学师郭黛勒夫人,我就协助她一起制备放射源。在清华学到的吹玻璃技术,这时也发挥了作用。由于我工作主动肯干,又比较虚心,所以郭黛勒夫人就对实验室里的其他人说:“你们有什么事做不了,要人帮忙的话,可以找钱来做。他有挺好的基础,又愿意效力。”人家问我,你为什么要这样干?我说我比不得你们,你们这里有那么多人,各人干各人的事。我回国后只有我自己一个人,什么都得会干才行。例如放射源的提取,我自己不做,又有谁能给我提取呢?所以样样都得学会才行。
这样,我在实验室里待了两年,增加了不少知识和技能。1939年初,伊莱娜·居里夫人又给我一个课题,让我协助她测定铀和钍在中子轰击下产生的放射性镧的β能谱,以证实是相同的裂变产物。
进退乏路
但实验室外面的局势,却总使我心中十分不安。中国正受到日本的侵略,我的父亲也由于忧愤过度而与世长辞了。我那时还不太清楚法国战败的严重程度,事实上德国已逼近巴黎。有一天,经法国友人的提醒,我们也开始了逃难。所谓逃难,就是骑上自行车,向巴黎西南方向逃去。走了两天多,就不能往前走了,原来德国军队已赶在前面,把我们这些巴黎难民都拦住了。于是,只好又坐火车折返巴黎。我回到巴黎之后,心情很是沉重。不但祖国被入侵,家园沦陷,法国也落入希特勒法西斯之手了。进退乏路,报国无门。再有,就是现实的困难,到8月份,中法教育基金会的公费就断了。回国不行,留下来也没有生计,怎么办呢?
有一天,我在一条小路上散步沉思,突然抬头看见约里奥先生正向我走来,我吃了一惊,因为我没想到他也没有走。事后我才知道,弗莱德里克·约里奥和伊莱娜·居里夫妇原来是决定要走的,并且已经离开了巴黎,到了法国南方的克莱蒙弗朗,准备上船。可是,临时他们想想不能走。“我们走了,法国怎么办?”于是,他们把当时能够弄到的重水(重水是当时认为可能制造原子堆所需要的重要材料)托付给两个可靠的学生运走,自己却回到了巴黎。我向约里奥先生诉说了自己的处境。他听了之后说,只要我们自己能活下去,实验室还开着,就总能设法给你安排。当时约里奥-居里夫妇尚可以支配居里基金,就把我留到她的实验室继续工作了。
巴黎沦陷后,德国人也占领了法兰西学院的核心化学实验室。名义上占领这个实验室的是德国的核物理学家玻特教授,也有盖世太保在实验室监视,但一般情况下不干涉约里奥-居里及其手下人的科学工作。约里奥先生做学术报告时,玻特教授也来听听。表面上似乎和平相处得不错,所以社会上有一种说法,说约里奥先生与德国人“合作”了,意思就是妥协投降了。但实际上,约里奥先生却在从事地下救亡活动。约里奥先生的助手和学生中,许多都是法国共产党的党员。就这样,约里奥-居里的实验室,表面上是处在德国占领之下,实际上却是地下活动的据点。
再回居里实验室
我在沦陷后的巴黎度过了1940年和1941年。虽然在科学工作上又有了不少长进,但心中总是很不安,一直思念着自己的祖国。这时,从里昂方面传来一个消息,说法国南方还有船开往中国,但不定期,要等机会。听到有这种可能性,我就决定回国。1941年底,我从巴黎来到里昂,在那里暂停,住在中法大学宿舍里,打听船的消息。谁知道一打听又说是走不成了,根本没有这种可能性。里昂大学物理系有个物理研究所,我就到那里临时做点工作。
因为法国当时被分为“自由”区和占领区,巴黎属于德国直接占领地区,而里昂却属于维希政府(傀儡政府)管辖的地区。来往于两者之间是要签证的,我已不容易回巴黎了。
我给约里奥先生写了一封短信,问问情况。当时伊莱娜夫人身体很不好(与她的母亲一样,是受了放射性的影响之故),每年冬天都到法国瑞士边境的一个疗养区休息养病。她在疗养地(属于“自由”区)写信给我,约我去谈谈。我到那里去陪伴了她两三天。她说既然你回国无路,只要你愿意,约里奥可以帮你弄到回巴黎的签证。1943年1月,我得到了签证,回到巴黎,在居里实验室继续进行我的研究工作。
总起来说,我在居里实验室的头八年中,从一个对原子核科学尚未入门的青年,逐步成长为能够独立进行前沿研究的科学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