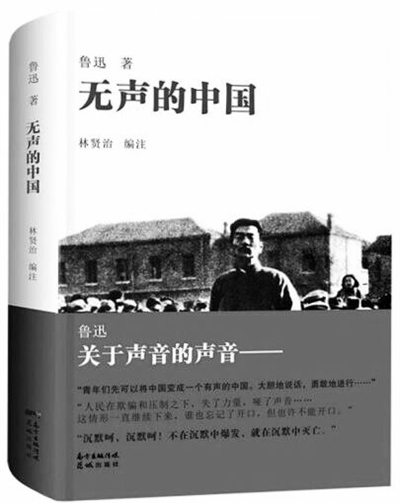
《无声的中国》鲁迅著林贤治编注花城出版社2022年1月出版 鲁迅的声音是丰富的,他所倾听的声音也是丰富的。这里把富于声音的文字汇集到一起,使阅读时,视觉之外,加强听觉的作用。我们可以循声寻找鲁迅,寻找鲁迅的经验,他在一个黑暗的时代里的所见、所闻。
1927年1月,鲁迅南下广州。2月,他应邀到香港做了两次演讲:头一次名为《无声的中国》,再一次叫《老调子已经唱完》,都跟声音有关。
数年前,我为花城出版社编了一种鲁迅的散文随笔集,为方便计,就以《无声的中国》命名。书的销量尚好,编辑告诉我,拟于近期重印。我便借此机会,做了较大的修订:一是把小说和别的文类收进来,二是内容多少跟声音有关。
鲁迅(1881-1936),一生横跨两个世纪,在世却只有短短的五十五个年头。然而,他却为人类留下了一笔巨大的思想遗产。作为一个清醒的启蒙主义者,他的思想是属于底层,属于旷野,而与当时国家意识形态相对立的。
早在留日时候,青年鲁迅便寻找并引进域外的“新声”。在《摩罗诗力说》一文末尾,他发问道:“今索之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然而,他听不到有“先觉之声”“破中国人之萧条”,唯有一片沉寂。
辛亥革命的风雨过后,中华民国为北洋军阀所劫夺,北京陷入一段相当长的黑暗时期。其时,他读佛经,抄古碑,暗暗地消磨生命。《新青年》的编辑朋友前来动员他做文章,有如下著名的对话: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这是启蒙者的声音。
“五四”过后,启蒙运动退潮,学生爱国运动及工农运动随之高涨。鲁迅在学潮的起落间度过了几年,至“三一八惨案”时,他由空洞的“救救孩子”的“呐喊”到直接为受压迫、受驱逐、受虐杀的学生代言,不惮于反抗政府,与知识界的“正人君子”者流展开私人论战。
北京政治环境恶劣,鲁迅于1927年1月来到“革命策源地”广州,任教于中山大学。不出半年,遭国民党“清党”,遂“为梦境所放逐”,年底定居上海。此间,一方面他说被杀戮吓得“目瞪口呆”,另一方面却不曾间断抗议的声音,正如他所宣称的: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野草》题辞)
在上海的最后十年,鲁迅曾经加入过一些团体,如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但是,实际上,他一直坚持独战。这时,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对于言论出版的审查控制日益严酷。鲁迅不得不使用多个笔名,在专制独裁政体下开始“隐微写作”,创造了一种如他所说的“吞吞吐吐”“曲曲折折”的反抗的奴隶风格。对于一个知识分子作家来说,失去自由言说的权利是十分痛苦的;鲁迅却认为,这正是广大被奴役的人们所承受的命运。
30年代以后,鲁迅的处境愈来愈坏,甚至在“左联”内部也受到压迫,致使他不得不“横站”着作战。1933年以后,他信中常常出现“寂寞”“苦痛”“焦烦”“寒心而且灰心”一类字眼,那是搏噬之后,躲进深林里舔自己伤口的野兽的声音。
对于大时代的变动,他曾经这样述说他倾听的经验:
我们听到呻吟,叹息,哭泣,哀求,无须吃惊。见了酷烈的沉默,就应该留心了;见有什么像毒蛇似的在尸林中蜿蜒,怨鬼似的在黑暗中奔驰,就更应该留心了……
鲁迅是善于倾听的。他不但倾听大地,倾听人民,也倾听自己。它既是时代的声音,也是内心的声音。这两种声音在他的著作中贯通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