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视剧《大宅门》里面的李香秀

养母郭榕和郭宝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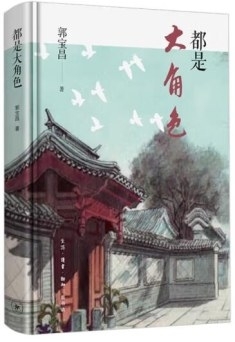
(摘自《都是大角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6月出版)
电视剧《大宅门》剧本的创作过程十分坎坷,稿子四次被毁。传言甚多,在网上也被描绘得五花八门,特别是有很多文章提到了电视剧片头字幕的最后一幅衬底,画着一个人跪在大宅门前请罪,说那就是我,由于外扬了家丑,向宅门族中人请罪。
惹怒了母亲
任何一部写人物的作品,人物大多有原型。我只向母亲认罪,那一跪只向我的母亲。在写《大宅门》剧本时,我一直是带着这样沉重的心理负担进行创作的。因为母亲曾表示过,离世以后不想在人间留下任何痕迹,我未尊母命,此乃大不孝。
我16岁上高中二年级时,开始写《大宅门》,是写小说。母亲发现我天天熬夜写东西,母亲以为我很用功。可高二时,我五门功课不及格,蹲班了,母亲怀疑了,那么用功怎么会蹲班?有一天放学回家,母亲脸色很不好,指着我的小说手稿问,你在写什么?我说小说。母亲说,你胡写什么?什么老爷太太小姐,抱狗的丫头。我急了,您怎么能偷看我的东西?“偷看”俩字,惹怒了母亲。第二天回来,我发现手稿不见了。
可创作的欲望始终使我无法住手。上大学以后我又动笔了,因为我把大宅门的故事向我的恩师田风教授讲过很多,老师觉得是太好的素材了,叫我写成电影剧本。所以第二稿写的是电影文学剧本,只在学院写,是完全背着我母亲的,那时满脑子都是揭露资产阶级丑恶的剥削本质。有关母亲的过往,这一稿中是没有的。
李香秀的原型就是我母亲
1970年在干校,我写第三稿,夜里偷偷地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写。这一稿其实是素材整理,把所有素材写成一个个的小故事,连顺序都没有,想到哪儿写到哪儿,一年多差不多写了厚厚的一个笔记本。
直到1980年,写了有十几万字了,与妻子分居一年后闹离婚。法庭上分家时我什么都没要,净身出户,只要小说手稿,前妻说烧了。从16岁到40岁,多少年?24年。写了四稿,一字都没留下。我心灰意冷,彻底地失去了激情。先放一放。由于恢复了工作,我要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从1976年到1995年的20年间,我没休息过一天,一共拍了8部电影,15部电视剧,写了8个电视电影剧本。到了1995年达到了创作的巅峰期,最佳的创作状态,决定塌下心来光明正大排除一切干扰正儿八经地写《大宅门》了。
1995年春节过后,我开始写《大宅门》。每天七点起床,八点准时坐到书桌前写剧本。夜里12点准时睡觉,不参与任何社会活动,不接见任何亲朋好友,冰箱里装满各种熟食,烧一大壶开水。我坚持了四个半月,完成了52集剧本《大宅门》(后改成40集)。当时单位里什么分房、定级、涨工资,一律舍弃。此时母亲已于1978年去世了,从写作上应该没什么障碍了,按说也不该有什么顾忌了。当第30集开始写到李香秀这个人物出现时,我心里就嘀咕起来,母亲当年的怒容历历在目,这个角色的原型就是我母亲。于是每场戏,每句词,每个动作我都字斟句酌、小心翼翼,绝不能让母亲挑出一丝一毫的毛病来。
我把对母亲的怀念、敬仰、深深的爱都寄托在这个人物身上了。后来网上有人评论说,因为李香秀这个人物写的就是作者本人的养母,所以塑造得特别完美。这话说得没错,这又是整个故事情节主线之一,前面又有二奶奶、黄春、白玉婷、杨九红一系列女性人物争奇斗艳,所以香秀这个人物塑造起来难度极大,至少得与前面的女性角色有一拼,我在每个细节上下的功夫也就特别大,当写到七爷与香秀定情一场时,我真的满意极了,得意极了。
老太太饶了我了
这场戏一写完,我如释重负,终于把最难写最发怵的一场戏,如此精彩地完成了,把笔往桌上一扔,直起腰往椅背上一靠,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就在此时我右肋下面猛地一阵刺痛,我忙用手摁住,以为揉揉就好了,可不行,钻心地痛,好像是肝儿痛。疼得我满身大汗,衣服湿透,在床上翻滚了几下,已是疼痛难忍。心想坏了,肯定是哪出了大问题,必须去医院。那会儿还没有手机,我勉强够到床头柜上的座机打给我常年包车的一位司机师傅,是我当时在京最信任、最亲近的人了。打通了,我已经没力气说话了。
当时心里只有一个想法,死期到了。也就十几分钟,小徐师傅来了,一看就傻眼了。我说去医院。小徐师傅说,去医院可以,可我必须叫人来,郭导,您现在这个样我负不起这个责任。我明白。可我除了还在深圳工作的妻外,再无亲人。儿子远在非洲。还有一个人是《大宅门》剧本顾问,所谓顾问,我专门请了三个人,每星期天聚在一起,看剧本,侃内容,然后谈感想。王先生就是其中之 一。
一见到王先生,我突然警醒了,他们正要把我往楼下抬,我忽然摆摆手,叫他们别动。我对王先生说,刚刚写完一章你去看看,王先生是个绝顶聪明的人,看完剧本走到我跟前说,明白了,宝爷,把这一章删了吧,这是不叫写呀,要不然把整个这条线删了。我也明白了,说行了,别管我了。你们都走吧,大家都愣住了,这怎么行?我急了,用尽最后的力气吆喝道:“走!快走!”大家吓住了。全走了。我艰难地爬起来,打开橱柜,从相册里取出了我母亲年轻时的一张照片摆在床头,对着照片我盘腿而坐,用个茶杯死死顶着我的痛处就跟我母亲聊上了,聊到激动处,我愤怒地号叫着。真是不可思议,号完不久,不疼了。电话响了,是王先生问怎么样了?我说没事了。王先生没听懂,我说我把老太太的照片请了出来,我跟我妈聊了会儿天,撒了个娇,老太太饶了我了。
每年清明扫墓,我都要与母亲聊上一阵,聊天的第一个内容,固定的是《大宅门》的事儿,向母亲忏悔、认罪。于是电视上便有了那幅长跪不起的画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