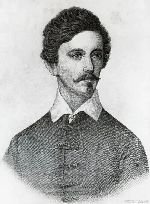
1929年5月,青年诗人殷夫将他的诗作和译稿投给鲁迅编辑的杂志《奔流》,其中一篇译文《彼得菲·山陀尔行状》引起了鲁迅的注意,他致信给殷夫讨要原文,因邮寄不便,殷夫便亲自登门给鲁迅送来。鉴于殷夫“如我的那时一样”,是“热爱彼得斐的诗的青年”,鲁迅特意写信给远在北京的许羡苏,嘱她往北京寓所找出“所藏的两本集子”,送给殷夫。孰料两年之后,“朋辈”成为“新鬼”,那两本书也“落在捕房的手里”“明珠暗投了”。
鲁迅的“情结”
四年之后,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言及此事也不胜悲夫。所谓“两本集子”都是裴多菲的作品,为鲁迅负笈留日译介《域外小说集》并创作《摩罗诗力说》的“三十年前”,因为热爱裴多菲“特地托丸善书店从德国去买来的”,一直珍藏,可见对裴多菲情结之深。恐怕鲁迅自己也没有想到,正因为他自1907年以来的这种“情结”,在有意无意间促成了裴多菲在20世纪在中国的译介、传播和经典化历程。
早期裴多菲的诗歌以民歌及其变体为主,取材自民间,偏重民谣风,具有很强的“人民性”。1846年的《云》将他在革命前夕郁郁寡欢、彷徨失望的情绪倾吐出来,之后他诗歌创作开始转向,并来到高峰期,革命与爱情成为这些诗歌的主题。他用诗歌描摹现实、控诉政府、赞扬革命,在人民中间有立场、有效力、有影响,他牺牲后,阿兰尼·雅诺什、谭启奇·米哈伊和艾米克·古斯塔夫整理并出版了他的诗文集,而早在1846年,这些诗就已经被翻译成德语,并随着日本“明治维新”之后“西学东渐”的潮流,来到日本。也就是在这股潮流尚未散褪之时,鲁迅和周作人都在日本接受“西学”思潮,注意到了“摩罗诗人”裴多菲,先是1907年周作人在《天义报》发表了《裴彖飞》,然后鲁迅又根据《匈牙利文学史》撰写了著名的《摩罗诗力说》,于是19世纪的匈牙利诗人和20世纪的文学家在异国他乡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的距离不期而遇了。
吊诡的是,自从鲁迅写完了《摩罗诗力说》,几乎很少译介裴多菲,直到1925年才翻译了几首裴多菲诗,在《语丝》发表。可是在得知殷夫和孙用等人也要译介裴多菲时,他依然倾囊相赠,倾其所有极力促成后来的青年将他们所译的裴多菲诗文发表,他认为殷夫和他一样,是“热爱裴多菲的青年”,所以才鼓励他、提携他、帮助他。不可否认的是,虽然当时“情随事迁,已没有翻译的意思了”,但是裴多菲依然深深地藏在鲁迅的内心世界,已经成为他的一种情结。
而这种情结的逻辑起点正是20年前鲁迅所撰《摩罗诗力说》,鲁迅那里,裴多菲首先是一位革命家,其次才是诗人,所谓“摩罗”,在裴多菲身上多数指的是革命浪漫主义精神,而不是具有现实主义意味的诗,鲁迅更关心的是作为革命者的裴多菲,是“行动”与“反抗”。在鲁迅看来,裴多菲的人格大于诗格。
对裴多菲诗人身份的建构
如果说鲁迅完成的是对裴多菲作为“革命者”的身份建构,那么茅盾、孙用、殷夫等人完成的则是对他诗人身份的建构。茅盾一直深受鲁迅和周作人的影响。1921年,作为主编的茅盾在《小说月报》开设了“被损害民族专号”,4月中开始与鲁迅通信,先是通过孙伏园,后来则直接向鲁迅约稿,鲁迅也欣然应约,至少寄给茅盾两篇译文;同时,他也将“被损害民族专号”的译文题目发给周作人请其“便示”。裴多菲当然是茅盾译介匈牙利文学的选择之一,茅盾不但翻译了《私奔》和《匈牙利国歌》,而且还撰写了一篇题为《匈牙利爱国诗人裴都菲》的文章,在言说诗人平民主义立场的同时,也开始注意他“诗化抒情”的外在形式。同时,茅盾还鼓励《小说月报》作家群一起翻译匈牙利文学,沈泽民、胡愈之等人都翻译过裴多菲的诗。
比之于茅盾,孙用对裴多菲的译介更为丰富。孙用1925年在《语丝》上读到鲁迅翻译的五首裴多菲诗,后来又在《坟》中看到《摩罗诗力说》,受到震撼,就尝试着给《奔流》投稿,得到鲁迅的注意和帮助。1928年,孙用得到了一部世界语版本的《勇敢的约翰》,爱不释手,花了很长时间翻译,并寄给鲁迅,打算发表在《奔流》上,鲁迅回信说《奔流》“有停滞现象”,认为“作者是匈牙利诗人,译文又好,可以设法印一单行本”,不但如此,鲁迅还将《校后记》和“注解”及有标注痕迹的修改稿都一并寄回来,使孙用不胜感激。孙用当时只是一个小小的邮务员,受到鲁迅的关怀,这对其鼓舞可想而知,从1930年代开始,他一直坚持翻译裴多菲的作品,前后持续了20多年,成为译介裴多菲最多的人。
把全部的裴多菲呈现在中国
就在孙用开始进入裴多菲译介高潮期的1930年代,很多译者开始译介裴多菲,梅川、林语堂、赵景深、金素兮等人要么直接翻译他的诗歌和小说,要么撰写介绍他创作的文章。及至抗战爆发,裴多菲的弱势民族国家诗人身份被格外凸显出来,也成为上海、重庆、桂林、永安等地文学期刊上频频出现的诗人,当时,李微、马耳、企程等都有译介,其中覃子豪的译介最多,后来将所有裴多菲诗结集起来,是为《裴多菲诗》,1940年代由浙江金华诗时代社出版。当时一批又一批翻译家前赴后继,使鲁迅想做但因“情随事迁”并没有完成的事业一直延续下去。不能否认的是,比之于文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裴多菲的革命精神对当时有识知识分子的影响尤甚,殷夫就是其中之一。
实际上,殷夫所译裴多菲的作品并不是很多,惟1929年刊于《奔流》上的八首诗歌而已,后来他又把大量的时间和热情都放在了投身革命上,无暇译介。历史的巧合之处就在于,如果不是鲁迅在怀念故人整理遗物时偶在《彼得斐诗集》的书页中用钢笔书写的《自由与爱情》的译文,恐怕后人也没有今天这般知道或者了解裴多菲。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原原本本、明明白白介绍了这桩往事,而且,这篇文章早在1949年就被收录到解放区的语文课本中,使一代又一代的读者通过阅读鲁迅了解裴多菲。新中国成立之后,仍然有人继续孜孜不倦地译介裴多菲,戈宝权先生就曾深情回忆他在莫斯科工作期间初见《裴多菲全集》及传记作者的激动之情。1950年代赴匈牙利留学的兴万生、冯植生诸位先生或是译介裴多菲诗,或是撰写《裴多菲传》,或是编译《裴多菲文集》,几乎把全部的裴多菲都呈现在中国,形成一笔巨大的中国遗产。
(摘自12月9日《文艺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