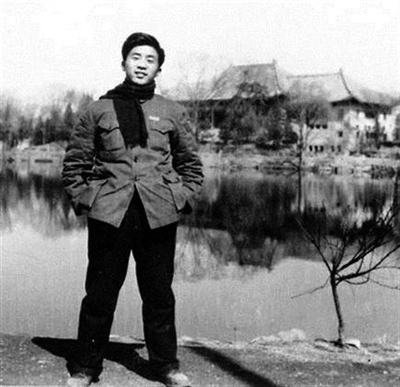
在北京大学期间的柳鸣九
12月15日,我国著名的文艺批评家、翻译家、散文家、出版家,我国法国文学研究领域泰斗级人物,第一个把萨特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来中国的中国学者,最后一部翻译作品是深受中国小读者喜爱的《小王子》的翻译家,自喻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的柳鸣九先生,在北京去世,享年88岁。
“中国萨特研究第一人”
萨特走红中国,得感谢毕生从事法国文学研究、翻译的柳鸣九。
柳鸣九以独到而富有前瞻的眼光,看到萨特“存在主义”的哲学价值,看到萨特哲学在中国的社会价值。198 0年,柳鸣九在中国学界颇有影响的《读书》杂志7月号发表《给萨特以历史地位》,他大声疾呼:“萨特是属于世界进步人类的”“我们不能拒绝萨特所留下来的这份精神遗产,这一份遗产应该……由无产阶级来科学地加以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一呼声如石破天惊,让中国社会的目光投向了塞纳河畔的那位法国学者。
1981年,柳鸣九主编的《萨特研究》出版、1985年再版。“萨特”走红中国,是改革开放之后一个显著性的文化事件,对外文化交流中一个标志性的文化现象。柳鸣九先生也因此被学界誉为“中国萨特研究第一人”。
必须承认,柳鸣九对萨特的理解超过一般人。萨特是一把钥匙,柳鸣九也是一把钥匙,一把“中国式钥匙”,他让我们知道除了物欲、功利,还有一种存在叫“精神”;他让我们知道了要在生动实践和火热生活中实现自我的价值,不要当社会的旁观者、时代的冷漠者。
柳鸣九不仅是满腔热忱的引荐者,还是训练有素的质疑者、充满锐气的批评者。上世纪三十年代,前苏联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日丹诺夫认为欧美文化是“反动、腐朽和颓废”的,这种“日丹诺夫论断”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对欧美文学的态度。
经过数月的充分准备,在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冯至的支持下,柳鸣九于1979年在第一次全国外国文学规划会议上,做了一个长达五六个小时的长篇发言,对“日丹诺夫论断”发起猛烈批判,起到了打破坚冰、解放思想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柳鸣九又是一位挑战者、拓荒者、清道夫、建树者。
四大领域耕耘播种
柳鸣九有自己的文化理念,那就是“为丰富社会的人文书架而作贡献”。他坚信尽管这个世界芸芸众生利来利往、名来名去,但“人文书架”依然是国人“精神骨骼”的支撑;他笃信这个速朽的时代、速忘的时代、速食的时代,仍然是一个需要经典、需要人文精神的时代。于是,他像一头辛勤的老黄牛,在文学创作、文学翻译、文艺理论、文学编著四大领域耕耘播种,成就了自己作为著作家、翻译家、研究家、编辑家的权威地位。
柳鸣九主编的《法国文学史》《法国二十世纪文学译丛》《外国文学经典》丛书、《雨果文集》(20卷)等,翻译的《雨果文学论文选》《莫泊桑短篇小说选》《都德短篇小说选》、加缪的《局外人》等相继出版、再版,15卷本、600多万字的《柳鸣九文集》问世,各类独著、编著、译著达三四百种。柳鸣九不是“著作等身”,而是著作“超”身了。每每有人以此恭维柳鸣九,这位谦逊、自信倔强的湖南人会说:“我是一个矮个子。”
拿起笔来是国王,放下笔来是草民,这大概是柳鸣九的人生境界。生活中的柳鸣九是一位闲淡隐逸之士,一个名利淡泊、与世无争的谦谦君子、优雅名士,好用“阁下”尊称对方,用辞谦和讲究。柳鸣九不是能向任何人都鞠躬90度的人,但决不是微倾一下敷衍客套应付之人,45-60度是他礼敬他人的常态。
柳鸣九好用法国十七世纪思想家布莱兹·帕斯卡尔“会思想的芦苇”来自喻,脆弱却有自重。他喜不形于色,怒不表于言,从不蹈之舞之、张之狂之,遇到冒犯、轻薄,耄耋之年的他最大反抗和愤怒常常是:“再也不给你们写稿了”或者“这是我给你的最后一篇稿子”。在语言暴力泛滥的今天,这种“柳式反抗”显得多么苍白绵软而又文质彬彬,但有力量。
晚年为孙女翻译《小王子》
柳鸣九十分看重亲情,曾用饱蘸情感的笔墨记述了作为一位父亲对儿子、一位祖父对孙女的爱恋深情。在文中他如过电影一般回放着儿子柳涤非从呱呱坠地到远赴美国求学创业、成家立业的过程,不无痛楚地倾诉了老年失子的心境……而柳鸣九一句写纪念文章“是为了给小孙女留一个她爸爸的记忆”,让人读到一位老人的内心强大与高尚。
儿子走了,为柳鸣九留下了一个可爱的小孙女,那是他内心深处的柳暗花明。2006年,由柳鸣九翻译的《小王子》出版,扉页上留下一行字:“为小孙女艾玛而译”,简洁却深情。10年后,《小王子》以新面目出现在读者视野,是老祖父柳鸣九翻译、小孙女柳一村插画的共同作品,老祖父特地写代序、作后记、附散文,情透纸背,心在泪中。
柳鸣九有另外一个孙女,虽然没有血缘。她叫晶晶,是安徽保姆小慧夫妇的女儿。小慧在柳家服务了40年,无微不至地照顾柳鸣九和他的夫人。小慧在柳家结婚,晶晶在柳家出生、成长,在柳先生资助下赴美国的大学攻读生物医学专业。柳先生甚至留下遗嘱,百年之后将房子馈赠小慧一家。
远观日出日落,近瞰潮起潮降,柳鸣九像那个遨游在七颗星球之间的“小王子”,既辛勤,又超越。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中,那位韩麦尔老师告诫学生们说,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就好像拿着一把……钥匙”。 萨特是一把钥匙,柳鸣九也是一把钥匙。你需要或者不需要,它都在那儿。
(摘自12月19日《北京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