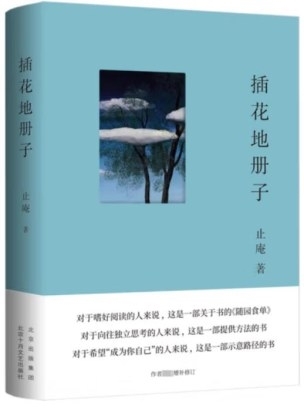
《插花地册子》 止庵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年9月出版 在本书里,作家与学者止庵(见图)回忆了自己的阅读经历,对印象深刻的作品逐一评点,又在时间的经度和地域的纬度间勾连比较,指出作品好在哪里,或者糟在何处,评论各书独具慧眼,不跟风,不故作高深,平易亲切,耐人寻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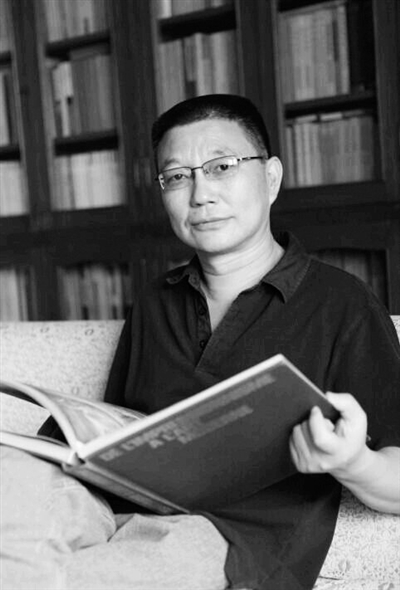
编故事给自己听
1973年夏天,父亲在家闲居无事,起念要教授子女们学习写作。我们兄弟姐妹经常聚在院里的槐树下,听他侃侃而谈。主要讲怎么写小说,也曾讲到散文,但是好像没有人提出要学写诗。大哥和姐姐都曾记有笔记,可惜未能保存下来。我那时还小,只能算旁听生,可是若论习作,却要数我写得最多,大哥和姐姐大概各自只写过一两篇东西,二哥有一次也说要写小说,但是起了个头儿就停笔了。那时他们户口都在乡下,前途未卜,也难得集中心思;我却多少有点儿无忧无虑。我写了几个短篇,取材于学校生活,故事多半是父亲代为编就,无论主题还是人物设计,都遵循当时“三突出”之类正统观念。他还曾挑了两篇分别代投给《北京日报》和《北京文艺》,但是都被退了稿。
这里有段插话,即二哥和我有段时间曾经写着玩儿过,但这其实与所谓“创作生涯”无关,只是我们之间的一种游戏。他年长我五岁,是我当时唯一的游戏伙伴。先是在棋子上贴些编造的人名,演习类似《东周列国志》的故事,不过国度和情节都出乎自己的幻想。后来觉得写下来更有意思,于是就你一段我一段地记在小本子上。二哥在乡下读过一部《荒江女侠》,回家来又借到《七侠五义》《小五义》《续小五义》等,特别投入,自己不免手痒,于是幻想国的故事写了一半就撂下了,又来写武侠小说,仍是由我来配合。
开头大概是模仿《荒江女侠》,可这书我没读过,不知究竟,等轮到我写了,只好胡编起来。当时我很迷恋章回体的形式,也学着诌了几个对句。我家房子顶棚一角破了个窟窿,我们每轮流写一段,就爬上被垛把小本子藏到里面。有一次被父亲发现,他担心有违禁的内容,特地取下来检查一过,但并没有予以制止,大概是没有什么问题吧。其实我们自己也很谨慎,记得我给一个人物取名“徐汇青”,二哥接着写时,怕被人误会,遂一一改为“徐洹青”了。拢共写了六七回的样子,不知怎么中止了,这些本子后来也丢掉了。
但是以后赶上失眠的时候,我有个自我疗治的方法,就是编故事给自己听;这其实还是当年和二哥合编的幻想国故事的延续,虽然距离那时已经很久远了,就连二哥离家出走也整整22年了。这故事真长——或许是我想念二哥的一种方式吧。
满屋都是纸团
再过一年,我开始学写长篇小说。仍是以学校生活为题材,人物和情节也是父亲给设计的,书名叫作“阳光下”。整整写了一年,用的是父亲从黑龙江带回来的稿纸,一页300多字,总共将近有1000页。我从那时起养成个坏习惯,一张稿纸不能有任何涂改,写错字就团掉重写,结果扔得满屋都是纸团。
我最后重看这稿子,是在15年前,不免很是感慨,内容不必谈了,就连遣词造句也那么拙劣,真是把好端端的少年时光都糟蹋了,于是就把它给毁掉了。不过当初父亲却对我寄予厚望,专门给我写了一本《创作断想》,谈论小说的创作方法。这本书有六万来字,分主题、结构、人物、情节、语言、手法等章节,当然不免受到正统观念的影响,但其中对某些作品如《水浒》和鲁迅小说的分析,还是颇具独到之见的。
此后我又写了一部长篇小说,那时母亲在街道办的废品收购站当会计,一月挣26块钱,我便取材于她这段经历,写了北京一条小胡同里几家人的生活。她有一位同事,名叫杨嘉平,回民,是一位著名金石家的遗孀,她们都是落难在此,所以相当投缘。杨大妈病逝于1989年5月,我的《挽歌》中那句“还要为无名老妇写一行苦寒的诗”,就是纪念她的。
我开始写这小说是在1975年末,父亲要到重庆去,临走前帮助我编成故事提纲,我记在一个小本子上。当时我最崇拜老舍,也想用北京口语来写城市底层生活,但是发现《骆驼祥子》里的许多说法,与现在已经颇为不同,不能照搬,还得靠自己在实在生活中体会。于是就留心胡同里老头老太太们平时的说话习惯,随时加以记录,然后用在自己的书里。我写作时经常给父亲写信请教技巧问题,父亲的回信每封都有七八千字,实际上是一批论文,探讨的问题较之《创作断想》更为深入。
我写了大半年,只完成了计划的一半,有20多万字。接着赶上唐山地震,家中别无损失,唯独我在逃难之际把记有故事梗概的本子给遗失了,这小说的写作也就中断了。
过士行是我的第一个读者
在此之前,我的一部分兴趣已经转向写诗了。这里要提到过士行,他本是我二哥的棋友,同时喜好文学,于是和我也有些来往。1976年春天,他说颐和园有株紫玉兰开花了,约我一起去观赏。看过之后,又往后山和西堤一走。颐和园最近十几年我没有去过,听说修复了苏州街,但我想这么一来,当年后山那种残缺之美也就无从领略了。西堤更不知弄成了什么样子,那时可是一湾浅水,几树衰柳,有些荒野情趣的。玩了一天之后,我们相约要写诗以为纪念。
我已经读过一些诗,其中包括父亲的两本集子《故乡》和《初雪》,对他创体的八行诗很感兴趣,于是就用这种形式写了五首小诗,凑成一组。这是我学习写诗的开始,得到过士行不少鼓励,他该算得我这方面的第一个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