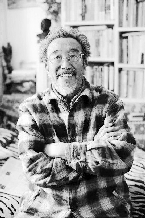

高莽1999年绘《普希金在长城》
上世纪80年代初,杨乐云先生已在《世界文学》工作了20多个年头,临近退休,开始物色接班人。当时,我还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读大学。通过文字、印象和长时间的通信,杨先生确定了我对文学的热情,问我毕业后是否愿意到《世界文学》工作。为让我更多地了解《世界文学》,杨先生安排我利用假期先到《世界文学》实习。
“要想成名成利,就别来《世界文学》”
1983年7月,我第一次走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大楼,来到《世界文学》编辑部。当时,编辑部有两间相通的大屋子,还有六七个小隔间。编辑部主任冯秀娟(诗人李瑛先生夫人)同秘书组,以及金志平先生负责的西欧组在大屋子里。其他人都分散在向南和向北的几个小隔间里。小隔间也就五六平米大小,主编高莽和副主编李文俊各自有个单间,其余编辑都是两人一间。
在过道里,正好遇见从小隔间出来的高莽先生(见图),他高大威武,身著沾有不少颜料的工装服,一副艺术家大大咧咧的样子,握手的刹那,突然大声地对我说道:“要想成名成利,就别来《世界文学》。”
记得有一次,几位前辈在为我们几位年轻编辑讲述编辑工作的意义。高莽先生以一贯的豪迈说:“马克思当过编辑,恩格斯当过编辑,列宁当过编辑,李大钊当过编辑,毛泽东当过编辑,周恩来当过编辑,历史上无数的伟人都当过编辑……”正说得激动时,李文俊先生轻轻插了一句:“可是,他们后来都不当了。”会议气氛顿时变得轻松和活泼。高莽先生毫不在意,也跟着大伙哈哈大笑。
而逢到节日将临,编辑部先是开会,然后就是会餐,算是过节。这一传统还是茅盾先生当主编时形成的。先生当时担任文化部长,兼任《世界文学》主编,公务繁忙,偶尔会来编辑部开会。每次会后都会餐叙。茅盾先生绝对是美食家。编辑部老主任庄寿慈也是。高莽先生独爱北京烤鸭,常常说:“发明烤鸭的人,应该得诺贝尔奖。”
跨界艺术家
高莽先生是那种你一见面就难以忘怀的人。高高大大的东北汉子,倒是同他的笔名“乌兰汗”挺般配的,总是一副艺术家的派头,说话时夹杂着东北口音,嗓门特别大。他翻译时喜欢署名乌兰汗,画画时才署名高莽。
凡是接触过他的人,都会被他的热情、豪爽、乐观、直率和善良所感染。外文所长长的过道上,只要他一出现,空气都会立马生动起来。倘若遇上某位年轻美丽的女同事,他会停住脚步,拿出本子和钢笔,说一声:“美丽的,来,给你画张像!”说着,就真的画了起来。他自称“虔诚的女性赞美者”。当然,他不仅为女同事画像,同样为男同事画像。单位里几乎所有同事都在自觉或不自觉中当过高莽先生的模特儿。
他总是调侃自己在编辑部学历最低。可这位“学历最低”的前辈却凭着持久的热爱和非凡的勤奋,基本上靠自学,在翻译、研究、写作和绘画等好几个领域取得了不俗的成就,绝对称得上跨界艺术家。他主持工作期间,常常有作家、画家、译家和演员来编辑部做客,大多是高莽先生的朋友。有段时间,为了扩展编辑们的艺术视野,高莽先生倡议举办系列文化讲座,并亲自邀请各路名家来主讲。我们都明白,这其中有着高莽先生的友情。
曾长期供职于《世界文学》的庄嘉宁先生在一篇文中为我们描绘了高莽先生举办纪念老《译文》五十周年茶话会的情形:
为开好老《译文》五十周年的会,高莽先生动用同仁的努力,请了当年老《译文》的撰稿人和《世界文学》的在京编委,他们是胡绳、萧乾、陈占元、唐弢、杨周翰、罗大冈、戈宝权,以及编辑部全体。高莽先生会前作了充分的准备,放大制作了一幅老《译文》第一卷第一期和陶元庆画的鲁迅先生像;另一张放大的当年老《译文》所有撰稿人译者的名单;与会者的签名也用大幅宣纸挂在墙上。这三幅当时颇有新意的作品随着岁月的流逝,成了文物,愈显珍贵。
记得戈宝权先生在签了到之后,站在这幅撰稿人名单前,随口就念到:“邓当世是鲁迅,菋茗也是鲁迅,玄珠、方璧、止敬都是茅盾的笔名……”我看见高莽停止了与另外来宾的问候寒暄,找我要了一支笔,随着戈宝权先生念出的名字,在名单上一一记下。会后,高莽将大幅鲁迅画像收了起来。十几年后调办公室时,撰稿人名单被我发现,完璧归高,他大喜。到会签名的那幅一直保存在编辑部。
这都是些了不起的人
记得刚上班不久,高莽主编就带我去看望冯至、卞之琳、戈宝权等编委。登门前,他都会买上满满一袋水果。
写出“我的寂寞是条蛇”的冯至先生有大家风范,端坐在书桌边,腰板挺直,声音洪亮,不管说什么,都能牢牢抓住你的目光。翻译出脍炙人口的《海燕》的戈宝权先生特别热情,随和,笑容可掬,亲自沏茶递水,让人感觉如沐春风。而卞之琳先生清秀,瘦弱,静静地坐着,眼睛在镜片后面闪着光,说话声音很柔,很轻,像极了自言自语,但口音很重,我基本上听不懂,心里甚至好奇:如果让卞先生自己朗诵他的《断章》,会是什么样的味道?
可以明显地感受到高莽先生对这些先辈的敬重和欣赏。正因如此,他也想让我们这些年轻编辑多多接受他们的教益,哪怕仅仅目睹一下他们的风采。这都是些了不起的人哪,他由衷地说。 (摘自崔建民主编《“作嫁衣者”说:中国社科院学术期刊编辑心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1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