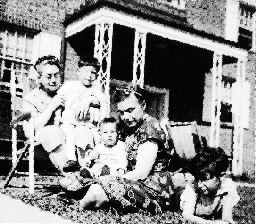
魏璐诗(右二)和儿子叶凯(右四)、叶伦(右三)
在上海宋庆龄陵园东侧,肃静的外籍人墓园里,安息着一位奇女子:魏璐诗。魏璐诗是出生在奥地利的犹太人,系维也纳大学毕业的哲学博士。但她一生最骄傲的是——“我是个中国公民”。
为上海而流泪
1933年9月,魏璐诗的父母亲为她远行上海深感担忧,她让父母放心,自己此行是作为短期学者去中国实地考察,并将自己在中国的内容做成节目,在维也纳电台播出。
初到上海,魏璐诗接触到的其实并非美好,而是令人厌恶的“震惊”。她以红十字医院名义,去检查工厂的工作环境,看到全是违规操作的“合法生产”:触目的破墙烂屋,工人蜷缩在鸽笼般的空间。
为这样悲惨的上海,魏璐诗流泪了,因为学习马克思主义,让她同情底层及反抗的民众。志同道合者开始向她伸出友谊之手。1934年下半年,史沫特莱寻她而来。魏璐诗这样描述第一次见面的史沫特莱:“个子瘦高,戴着一顶宽檐帽,低低地拉下来遮住脸。”史沫特莱比她大16岁,却“像一个热情四射的光团”。
宋庆龄的密友
上海香山路7号——曾经,这里是莫利爱路29号,为一幢砖木结构的欧洲乡村式小洋房。1935年农历新年,魏璐诗第一次上门,拜访居住于此的宋庆龄。
对这次见面,她印象深刻:在宋庆龄家中,她品尝了一道入味的华南小吃——杏仁乳。
和宋庆龄见面后,魏璐诗即成为“宋庆龄的密友”,彼此常见面,却又“颇为神秘”。因为在其研究的资料中,找不到一张魏璐诗与宋庆龄的单独合照,不见一纸两人的往来信件。但在宋庆龄与诸多外国友人的信件中,一次次充满情感地提起魏璐诗,关心她的行踪及个人生活状态。如多年后的1942年,宋庆龄给王安娜的一封信中这样表述:“我希望璐诗能来。我匆匆赶回来,就是盼望见到她。”
20世纪史沫特莱、魏璐诗、路易·艾黎、马海德……在30年代初中期的上海,他们这些同情中国革命的“洋人”,既是不畏艰险的逆行者,又是特殊的奋斗者,环绕在宋庆龄周围,尽其所能发出自己的光热。
魏璐诗一次次推迟回欧洲,最终无以归家。二次大战中,无数犹太人被德国法西斯屠杀。在惨死者中,就有魏璐诗的父母——他们在集中营离世。
与鲁迅一见如故
有一张1936年10月拍的照片。照片上,鲁迅坐中,身着深褐的长衫服,两颗葡萄纽扣在右胸襟处。一脸瘦削的鲁迅,眼睛望着自己的右侧,似在专注倾听,亦似舒眉微笑。被鲁迅注视的这位女子便是魏璐诗。
因为史沫特莱,魏璐诗见到了鲁迅。而鲁迅也与魏璐诗一见如故。魏璐诗多次见到鲁迅,还单独前往,到鲁迅“住在城市北边的排房里”。
魏璐诗最后一次见鲁迅在1936年10月8日。那天是在一个木刻展上,许多年轻的艺术家环绕着鲁迅,询问他对木刻作品的评价。
魏璐诗一生两次入中国籍,一次是1939年,一次是1955年。
魏璐诗一生爱过两个中国人,并在20世纪40年代嫁给了其中一位,诞下两个可爱的儿子。但最终,她爱的人沉湎于自己的专业技术,滞留国外。1951年,她离婚,带着两个年幼之子,“备尝艰辛”地从美国辗转回北京。 2006年,她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摘自2月16日《解放日报》 郑宪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