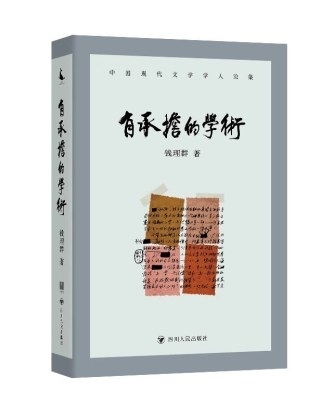
《有承担的学术》 钱理群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2023年2月出版
本书集中书写了二十余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文人学者。学者钱理群认为,在一定意义上,“学人”的影响比“学问”的传授更重要,更根本,更带基础性。
20世纪80年代,我来到北大校园,进入现代文学研究界,最刻骨铭心的,就是前代学人的学术与精神的熏陶:开始只是被动的赞赏、吸引,后来就变成自觉的研究和继承。而且如陈平原所说,我们这一代学人,最幸运的是,在学术研究的起点上,就与创建现代文学学科的,活跃在三四十年代学界的“第一代学人”相遇,直接承续他们的学术传统。
与此同时,作为“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批研究生,我们又得到了成长于五六十年代,正成为“文革”后学界主力的“第二代学人”的倾心扶植。这样,我们的“学人研究”,自然从对第一代和第二代老师辈的学术思想、观念、方法、风格的研究入手。收入本书的第一代学人中的王瑶、李何林、任访秋、田仲济、贾植芳、林庚、钱谷融的研究,第二代学人中的严家炎、樊骏、王得后、支克坚、孙玉石、刘增杰、洪子诚的研究,都是相应的成果。
我自己成长于五六十年代,我和洪子诚先生是同龄人,本应属于“第二代”;但我成为“学人”却是在80年代,也就自然被看成“第三代学人”。特别是我和远比自己年轻的黄子平、陈平原一起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就更被视为“青年学者”的代表了。直到21世纪,人们才赫然发现钱理群已经成了“老教授”:就像我自我调侃的那样,我是“没有中年”的学人。但我也因此有机会和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第三代学人”同呼吸,共命运,深知其执着的追求、承担与坚守,因此写下了收入本书的讨论赵园、杨义、吴福辉、王富仁等人的文字。
我在自己的第一部独立著作《心灵的探寻》题词里宣布,新的一代学人出现时,我将“自动隐去”,许多学界朋友,包括王瑶先生都觉得不可理解。尽管后来我也一直没有隐去,但那样的把希望寄托在“第四代学人”即我的学生辈的观念却十分顽固。我也因此把培养、扶植青年一代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责之一,自觉地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第四代学人开辟学术道路。
在退休,远离学术界以后,我依然在默默关注我的学生的学生,应该是“第五代学人”的学术与精神成长。不管怎样,我的广义上的“学人研究”也坚持了几十年,涵盖了五代研究者。现在编成这本《有承担的学术》,也算是一个交代,而且期待后继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