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与沈培(左)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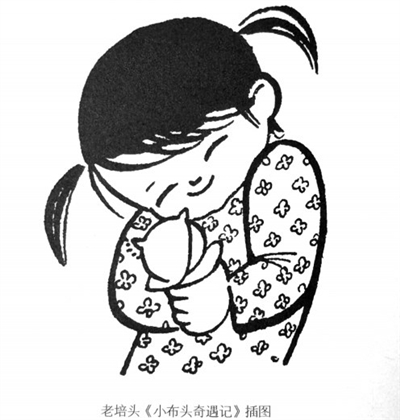
沈培《小布头奇遇记》插图
沈培年过九十,静静离去,不扰外人,正是他的本色。
“浪费多少纸张啊!”
案头一直摆着沈培写给我的一沓信,以及他的文集《孤山一片云》,他的传记《老培头》。信很多,读一遍却不费时,因为都短,少则七八字一二十字,多不过百字。比如 2015年1月17日:“家明兄:蒙赐三册《小艾,爸爸特……》。谢谢万分。忙安”;2016年2月16日:“家明兄:《存牍辑览》读毕。好书!兄《编后记》佳甚!有力写范传。文安”(“范传”即“范用传”。范用,出版家,沈培好友,2010年去世。我曾说退休后想写范用传,他极襄赞)。他写信,想到就写,并不在乎回信,有时连着写好几封;他的书写老派,自来水笔竖写繁体,署名也随意——老培,老培头,培金(他全名沈培金),而且前面全部加一谦词:弟。信写在A4复印纸上,其中常有夹带:漫画、照片、文章剪报,也都是复印件。有趣的是,20年的来信,清一色自制信封,是银行、供电局、煤气公司的通知单,封面有一块透明纸的那种,他用一绺白纸贴住封面,右下角的发信地址,是以图章的方式钤印:沈培金,寄自香港九龙油麻地……这些都让我想起范用。老先生们的做事风格竟是神似!
有一天他来信开头就说:“此信所言只做朋友谈,不外传,不反映。”我一惊,看下去:
我看到一本画册。上冠名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美术家会员图册”、XXX画家肖像,封底有“中国美术家协会、人民美术出版社编”字样。内页的画作,真不堪入目。浪费纸。但无标价,似并不涉成本和利润。是画家本人掏钱吗?总之,不分优劣,给美协会员出画册,真是馊极了的馊主意!浪费多少纸张啊!
我问了一下(其时我还不是社长),无法给他答复。但他不指责其他,唯反复叹惜纸张,给我留下印象。这与他惜墨如金、自制信封如出一辙。
短得不能再短
沈培给我的信,夹带最多的是他写的短文(手写复印件)。
那是2004年,老同学黄裳(此黄裳想必不是容鼎昌那个黄裳)编校刊,嘱他写校园回忆。“写了几篇。黄裳病,退出编校刊。回忆如水,漾出校园。拉之杂之,竟写出两百来篇”。
开初寄给我的都是国立杭州艺专的故事,上课、混玩,老师、同学:潘韵、丁天缺、江丰、丁正献、金冶、朱金楼、潘其鎏、周光中、戴先宜、周昌谷、张荣海、赵德萃、裘沙……有的人我知道,大多完全陌生,但各自有名有姓,都是小事、怂事、趣事甚至怪事。后来范围渐宽,从故家儿时到入艺专,到解放,到上海少年报、中国少年报,到港报,杭州、上海、北京、黄湖农场、香港九龙,一直到21世纪初,凡70年。天知道平凡日常中的妙人、妙事,怎么全被他看在眼里,记录在案。集腋成裘,俨然一部书稿。
韩羽看了说:“阿培哥的文,短得不能再短了(仅数十字)。文虽短,却颇耐人咀嚼。再说虽三言两语,却是亲历实录,不亦文即史乎。”
我知沈培有意出版,但正犹豫,小众文字,不知卖谁。四川张京有魄力,交给书虫吴鸿,2014年出书,沈培正好80岁。六年后,严向群的沈培传问世,加之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少年报创造的“小虎子”和为《小布头奇遇记》的插图,沈培这一辈子不算白过,堪可含笑九泉。
痴迷艺术
沈培爱艺术,那才叫真爱,那才叫痴迷。他见了好东西恨不得捧回家去,又恨不得让所有朋友看到;反之,看到不好的东西,疾言厉语,恨不得骂人(上面引用的信还是客气的)。斯坦伯格就是他的酷爱,我则成为他的传播对象,不但收到一整本画册的复印件,还送我一本购自美国的原版画册,从此我也成为这位罗马尼亚裔美国画家的崇拜者。
在三联书店工作时,我曾用斯氏的画印过一种非卖品笔记本,设计巧妙,广受欢迎。前几年终于从斯坦伯格基金会购得版权,出了一本画集,可惜设计不对,沈培不满。我汗颜,直想重做,迄今未果……
早年我在山东画报出版社出过挪威画家古尔布兰生的《童年与故乡》,沈培喜欢,他发现我所据版本不完整,特意复印了缺失的页面寄来,后来读库老六寻到德国原版,重印全本,精美绝伦。央美广军,沈培挚友,小沈四岁。广军风趣多智,能版画、漫画、油画,亦能作文,此等人精,沈培焉能不爱?焉能不介绍与我?2010年,生肖虎年,广军寄我自制贺卡,内容是一只老虎去武松开的饭店,武松问:客官想吃什么?虎答:想吃那年没吃到的——广军智趣可见一斑。沈培将广军文章荐给我,问可否编辑出版,我亦唯唯。
“手套绳断”
若说沈培好友,最是丁午。丁午也是央美毕业。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们一个在中国青年报,一个在中国少年报,都是美编,都画漫画,都属团中央,同住一间宿舍好几年。一同下放山东高唐农村种棉花,一同奔赴河南黄湖农场干杂活。形影不离,人称手套——用绳连着挂在脖子上的棉手套。
丁午在农场给留在北京的八岁女儿写信画画,第一封信就有他和沈培、梅青的“合影”(画)。1979年丁午调到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创办和主编漫画刊物。2011年我来人美社,去看望80岁的丁午,得知他在农场给女儿所写所画的60多封信,是自认为最珍爱成熟的作品。不久,丁午去世,我编辑出版了这些信件,名为《小艾,爸爸特别特别地想你》。我请沈培写了一篇短文,名即《手套》,印在书里。虽然只500字,但已是他少有的长文了。
这本书出版后,2012年初夏,沈培忽然寄我一本装订成册的漫画——丁午编画的《未迟的画》。未迟,沈培儿子。画中以小孩子未迟的身份发表意见,童趣横生。沈培附信说:“丁午画此册,迄今已近四十年。原稿十三页,归主人公沈未迟保存。限量复制十二册,送呈亲友……”我荣幸且喜欢,有次见到尚晓岚,推荐给她,她看了来信说:“《未迟的画》太有趣了!一激动就火速写了个东西。”不久,在《北京青年报》发了整版。沈培高兴,也赠她十二册之一。
其实细想起来,我和沈培没见过几面。早年他来北京,到我办公室,从未超过五分钟,连水都没喝过,更没一起吃饭。其做派堪称古怪,起初很不习惯,后来感慨,不是矫情,而是生怕耽误别人。
原本打算问他,《手套》一文结尾,“1980年,我南迁。种种隔阂,种种传言……如刀如剪,手套绳断”,他与丁午怎么了?未问。如今恐怕永久不解了。
(摘自7月17日《中华读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