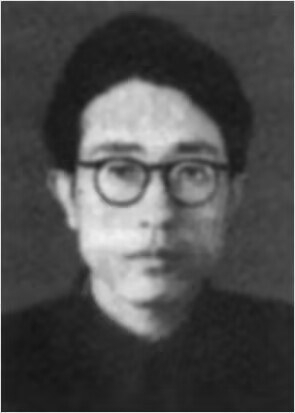
我第一次去哈尔滨,是1985年的岁末,那时候刚刚在沈阳考上研究生,随着导师王忠舜老师去拜访一位名叫鲁琪(见图)的诗人。
列车过了四平,便是一片苍茫,雪覆盖着黑土地,几乎看不到人家。王忠舜老师是满族人,民国期间在汉城(现在叫首尔)做过外交官。他对哈尔滨、长春、沈阳都很熟悉,朋友也多。他的前半生就很传奇,而结交的朋友,也多带有异样的色彩。他说,研究现代文学的,不太看好东北诗人,这小视了白山黑水的人们。像鲁琪先生,总还是要记上一笔的。
哈尔滨极冷,下车后,我的嘴冻得说不出话来。我们在一座老式的大房子里,见到了鲁琪先生。他站在门口,大概等了很久。看出来,他是一个不善交际的人。诗人已经60岁了,头发稀疏,瘦瘦脸庞刻满皱纹,话不多,内秀的样子里透出几分沉稳之气。他的夫人也是一位作家,显得年轻一些,跑前跑后地招待我们。
寒暄中发现,鲁琪并不愿意多谈论自己,知道我们来收集资料,似乎并没有多少兴奋。但也许碍于朋友的面子,并没有让我们吃闭门羹。只是随便闲聊,毫无重点,席间所谈,还是有不少我们期待的内容。
王忠舜老师与鲁琪是长春读书时期的同学,他们将近40年没有见面了。也许是因为王老师的外交官经历,见多识广,读人也有深度吧,他幽默的话语逗得鲁琪笑了起来,一起忆及解放前的时光,谁谁不在了,谁谁到了国外,还有散落在地方的朋友的近况。冬夜的书房里,一时显得暖融融的。
鲁琪是辽南人,1924年生于离复州城不远的盖州。他的创作始于40年代初,那时候日本占领了东北三省,家乡变成了“满洲国”。1942年,就读于伪满洲国新京王道书院,该院是溥仪的伪国务总理大臣郑孝胥倡议创办的,旨在培养忠君亲日的文职官员。年轻的鲁琪不久便感到了一种耻辱,一些感想便流露在文字中。他突然喜欢上了诗歌,作品也渐渐在报刊上登载出来。那些诗歌,都有点压抑,对于占领者的反抗之语清晰可见。但不久,他的诗作便被特务发现,以反满抗日之罪投入监狱,且判了死刑。
他的死期定在1945年8月15日。鲁琪知道大限将至,却显得异常冷静。这种心境,都在他的诗歌里表露出来。日子很快到了,却传来日本战败的消息,监狱的大门突然开了。鲁琪与几个“同犯”拥抱在一起,庆幸这一时刻的降临。终于可以自由地行走在自己的土地上了,一切都变了。从死神边走过的鲁琪,知道了以后自己的路应该在哪里。
大难不死的鲁琪,成了一个传奇,此后在自己的文字中,多了一些明快的色泽。当我与王老师深入了解了那段历史后,发现其身上带着诸多值得玩味的元素。
第三天再次到他家里时,诗人外出了,他的夫人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从其口中才知道,鲁琪搁笔有20多年。晚年的鲁琪专心于电影的写作,好像没有再去写诗。但读他的文字,还是很诗性的。
回到沈阳之后,我全身心地投入学业之中,但不幸的是,王老师忽然患病,手术后不久就去世了。过了多日,我就收到了鲁琪的信,语气显得很沉重,表达了对于老同学的怀念之情。这时候我才感到,应该尽快完成老师未做完的工作,于是与鲁琪先生商量,又去了一次黑龙江。
他的话照例是少,我问一句,他答一句。涉及20世纪50年代的历史,谈得不多,印象里讲到抗日生活时,话语才多了起来。在几次交谈里,隐隐地感到,我的到来,唤起了他的什么回忆,也许因为我也是辽南人,老人有一点亲切的感觉。他深思的样子很好看,吸着烟,面部被烟气所笼罩。他在狱中写下了不少诗歌,后来编入《狱中诗抄》,例如:
窗外,/有人吹着口哨过去了,/留下一段忧郁的曲子,/留给这拘谨的人。/他开始咀嚼/这怀忧的声调,/他那已将静止的心脏呦 ,/又做起忧郁的跳动。
这是多么悲壮的文字!阅读它,内心是被拽起来的,与之一同由幽暗中瞭望到远际的晨光。我由此联想起文天祥的句子,彼此多么神似。
研究生毕业后,我离开了东北。几年后,关于鲁琪的一本资料集终于问世了,内容主要限于20世纪60年代前的诗人行踪,大致可见一位坎坷的诗人之路。此书虽不尽如人意,但还是完成了老师的遗愿。 (摘自《随笔》2024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