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铁木前传》里的小满儿(张德育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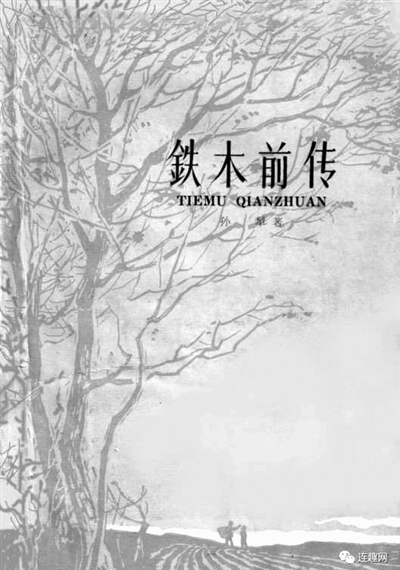
《铁木前传》封面
我多次面对媒体或朋友说,我的第一志愿并不是艺术,而是做一名交响乐队指挥,第二是作家,其次才是画家。这个莫名的摸不着头脑的幻想,来源于我的母校“中戏”。中戏是中央戏剧学院的简称。我出身村野少见识,自幼除家庭给予我那点“学问”和知识外,无其他见识。但母校中戏,不仅给了我艺术的方方面面,还成就了我一个杂家的风度,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对文学的热衷。是母校的“名著选读”课,和先生对此的苛刻要求,使我常常游历于那些名著之中,但眼前的人物大多是洋人:大卫·科波菲尔、聂赫留朵夫、玛丝洛娃、苔丝、格里高里和阿克西妮娅们……面对自己民族的认知,除几本古典名著外,当代作家的那些对一个激情时代的激励的描写并没有给我留下真切的印象,他们言语近似,与文学本身产生着距离。
无独有偶,孙犁先生《铁木前传》的问世,打破了我对当代文学的认知偏见。一群近在身边的中国人耀眼登场,它准确严谨地表现了一个民族在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生存状态。他们的出现使我脑中的大卫·科波菲尔们一时远离我而去。
在此之前我曾读过孙犁先生描写水乡白洋淀的系列作品,那时我就觉得在描写战争年代的作品中,它们已经别开生面、独树一帜了。我们从他的作品中看到了战争中一群真实的人,尤其战争中那些女人和她们的真实心思。她们朴实爱国,主张亲人们奔赴前线、同仇敌忾,但她们也有人类共有的那些细微的,细微到不为人知的情愫。如《荷花淀》中对水生和他的女人的描写:年轻的水生要告别年轻的妻子奔赴前线找大部队去。正在织席的妻子,没有豪言壮语式的表态,一时间出现的是女人那种特有的难以言表的、私密的内心颤动。年轻的妻子面对即将离家的年轻丈夫,孙犁只写道:“女人的手指震动了一下,想是叫苇眉子(苇眉子,织席所用破开的芦苇秸秆。白洋淀多芦苇,用芦苇织席是当地女人的家常)划破了手。她把一个手指放在嘴里吮了下。”这个独特的、出其不意的描写成就了孙犁的文学主张。几个出其不意、合乎逻辑的细节描写是可以把一位作家送进文学大家的行列的。如鲁迅对细节的慎重选择和出其不意的描写。
当然孙犁先生和我出其不意的沟通,还在于少年时相同的生活经历。他在《铁木前传》开篇时写道:
在人们的童年里,什么事物,留下的印象最深刻?如果是在农村里长大的,那时候,农村里的物质生活是穷苦的,文化生活是贫乏的,几年的时间,才能看到一次大戏,一年中间,也许听不到一次到村里来卖艺的锣鼓声音。于是,除去村外的田野、坟堆、破窑和柳杆子地,孩子们就没有多少可以留恋的地方了。
童年时代的我身边也不乏田野、坟堆、破窑和柳杆子地。
一本薄薄的《铁木前传》,给我打开了另一扇文学大门,我有过一本,书中还带有精美的插图。插图的作者是我的朋友张德育,但当时我并不认识他,只知道他在中央美院毕业后供职于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画一手兼工带写的水墨画,一幅名为《岭南风》的作品问世后,曾在美术界引起过一阵轰动,好像还在国外获过一个什么奖。后来便是《铁木前传》的插图,那是“文革”之前的事儿,“文革”之后,德育由于种种原因有意离开天津。经朋友介绍想来保定,当时我也住在保定,我们的认识和后来的交往就开始于此。但德育的意愿因故并没有实现,只留下我们之间的友谊和对于艺术、生活和时代一些散漫的话题。当然还是艺术多于其他。当时我尚是一个刚入门不久的艺术青年,而德育早已蜚声艺坛了。在谈话中,我常直截了当地问到他自认为满意的作品,他思考片刻,显出非常慎重和郑重地说:“《铁木前传》吧,《铁木前传》中的小满儿吧。”
他却不提他的被称作代表作的《岭南风》。《铁木前传》中的小满儿是孙犁笔下一个神秘莫测的年轻女子,作者在描写她时,显然带着十分复杂的混合感情,她年轻坦荡不满于眼前的现实,常带着几分热烈狡黠使人难摸的性情,于人于事。由此也会招来几分不雅的名声。插图的细节是这样的:一位下乡了解民情的干部住在她家,小满儿深夜来到干部所住房间。
孙犁写道:
干部利用小桌和油灯,在本子上记了些什么。他正要安排着睡觉,小满儿没有一点儿响动地来到屋里。她头上箍着一块新花毛巾,一朵大牡丹花正罩在她的前额上。在灯光下,她的脸色有些苍白,她好像很疲乏,靠着隔山墙坐在炕沿上,笑着说:
“同志,倒给我一碗水。”
“这样晚,你还没有睡?”干部倒了一碗水递过去说。
“没有。”小满儿笑着说,“我想问问你,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是领导生产的吗?”
“我是来了解人的。”干部说。
“这很新鲜。”小满儿笑着说,“领导生产的干部,到村里来,整年价像走马灯一样。他们只看谷子和麦子的产量,你要看些什么呢?”
干部笑了笑没有讲话。他望着这位青年女人,在这样夜深人静,男女相处,普通人会引为重大嫌疑的时候,她的脸上的表情是纯洁的,眼睛是天真的,在她的身上看不出一点儿邪恶。他想:了解一个人是困难的,至少现在,他就不能完全猜出这位女人的心情。
干部猜不出这女人的心思,也给读者留下了一个难题。
张德育准确生动,以传神手段描绘了此时此刻一个手端大碗直视着那位干部,目光单纯、犀利、天真而狡黠的小满儿。德育对作品是满意的,后来他带着这幅插图到孙犁家请孙犁过目。孙犁见图兴奋地招呼出他的老伴,然后两人同时问张德育:“你见过小满儿?”张德育告诉孙犁,他见过“小满儿”。其实德育虽也出身农村,但他是山东人,为寻找小满儿,曾专程深入冀中腹地,去寻找孙犁和自己心中的“小满儿”。小满儿终于在他心中诞生了。
孙犁意外地和他书中的人物“相遇”了。
一次诗人伊蕾女士邀我去天津参观她所经营的卡秋莎美术馆。那时的伊蕾刚从俄罗斯归国,收藏了不少俄罗斯和苏联艺术家的作品,之后陈列于她在天津开设的美术馆中。那天我也邀了张德育,其间问到他带插图去见孙犁时的情景。德育说就是那样。还说因为孙犁的老伴也是冀中乡下人,才想到同他老伴一起看插图,认可小满儿。
就像孙犁塑造了一个小满儿的原型,而张德育使小满儿的形象更加真切了。小满儿活了。
造型准确具有艺术价值的插图,可使一个文学人物形象的无限变得有限。就像苏联画家韦列伊斯基为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所作的插图。当著名导演格拉西莫夫为把作品拍成电影物色演员时,他是一手举着韦列伊斯基的插图去寻找演员的。拙劣的插图是对人物的败坏,也是对作品的败坏吧。在文学和书籍的汪洋大海中是不乏拙劣的插图的。
张德育对小满儿的成全,使孙犁对张德育也念念不忘了。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那个十年动乱之后),我因事去天津顺便拜访我的一位老乡李立。抗战时李立是我们那里抗日政府区长,常住我家,现在天津日报社做领导。据说他和孙犁住在同院,好像位于马场道一座大房子里。是个初冬的黄昏,我走进这个大院子,看见一位老者悠闲地袖手站在屋前。房子虽高大但不似天津那些洋别墅,也不似地道的中式建筑,它有高大的窗棂和木柱,在黄昏中显得很阴森呆板。老人见我进来,问:“你找谁,找我吗?”他声音浑厚,细听带着冀中腹地的乡音,我猜这便是孙犁先生了。我说我是来看李立同志的。他侧过身朝着大房子的另一边喊道:“李立,有人找你。”然后转过身来朝我观察一阵。于是李立从大房子的另一端走过来,呼着我的名字,又把我介绍给孙犁先生说:“赵县老乡,画家,我领导过的儿童团长。”孙犁接话说:“赵县属冀中六分区。”李立说:“后来的十一分区。”或许是孙犁听到李立对我画家身份的介绍,又朝我端详一阵说:“认识张德育吧?”我说:“认识,很熟。”其实这次我来天津就住在张德育家。
孙犁只“哦”了一声,向房中走去。这时我才注意到他过早地穿了一身不灰不蓝的旧棉衣。走着拍打着自己的衣服。拍打自己的衣服好像是乡下人的一种习惯。拍打衣服上的灰尘?或使棉衣变得更加松软?这使我想到,只有下意识拍打自己棉衣的“乡人作家”,才能写出鲜活的乡人吧——傅老刚、黎老东,还有九儿、六儿和小满儿。
可惜,那天我和与孙犁近在咫尺的李立,只谈了些陈年旧事,再没有话题谈到孙犁。李立只说早已看出我长大后将要落在文艺界,因为他教我唱抗日歌曲时,就发现我声音优于其他同学。还有他也看到过我在家中墙上用木炭画满的戏画……当我谈到《铁木前传》对我文学的启蒙时,李立才说:“那是一部新奇的作品,它永远新奇。”有战争经历又从事文字工作多年的李区长,是懂得文学的。
那天我回到张德育家,问到他插图的下落时,他情绪黯然地大口抽着烟说:“命都难保,还顾得上什么插图,不知去向。”它们毁灭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那场文化浩劫中。德育好一阵沉默。据我所知,当时的德育为插图可是受过一些磨难的。就像孙犁先生也为《铁木前传》受过磨难一样。
告别时,德育用桌上简单的笔墨宣纸为我画了一张“采莲图”,但画得散漫,远在《铁木前传》插图之下。
有时我觉得作家艺术家就像运动员一样,自己有过的高峰自己是无法超越的。
成全孙犁先生为文学大家的,或许就是围绕在小满儿周围的那个人群。当然还有水生,还有被苇眉子划破手指的那位年轻媳妇。 (摘自《中国作家》2025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