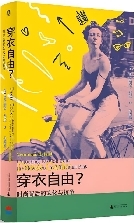
(摘自任瑞洁译《穿衣自由?:时尚背后的文化与抗争》,野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5月出版)
赋予的身份与联想
“具衣认知”是“假装即现实”这一经典概念的时尚版。科学也已证实,这种现象真实存在。
美国西北大学的心理学家让学生穿上白色长外套,并告诉他们这是医生的白大褂,结果学生在需要专注力的任务中表现显著提升。而当同样的白外套被描述为画家的工作服时,研究人员并未观察到类似效果。这表明拥有力量和权威的并非衣服本身,而是我们赋予其的身份与联想。但这并不是简单地等同于“穿上相应的制服即成为医生、军人或囚犯”,而是说制服是角色的一部分,穿上它便承担了该角色所代表的身份。
从外科医生到交通协管员,众多职业都要求穿制服,但这些制服在社会中被赋予了截然不同的含义。它们不仅象征着你的职业和地位,还代表了你对雇主或所属机构的忠诚。在职场、校园或宗教团体中,制服被用来抑制个性、强化忠诚。受创业文化的影响,最近似乎兴起一种人为的“平等”趋势——首席执行官和初级程序员都穿着同样平平无奇的帽衫。然而,着装上的差别并未消失,只是变得更微妙而已。
机构常通过着装要求来强化自身价值观。控制你的穿着意味着某种程度的行为约束,让你服从于组织。这种约束从学生时代就已开始,政界人士(不只是保守派)也支持校服作为学校管理纪律的工具。
比尔·克林顿在1996年国情咨文中表示,公立学校推行强制校服政策是有帮助的,“这样青少年就不再会为了名牌夹克而互相攻击”。
同年晚些时候,在另一场演讲上,他进一步强调,校服“能帮助年轻学生理解真正重要的是自己是怎样的人,从而有助于打破暴力、逃学、失序的恶性循环”。这种反时尚情绪贬低了风格作为自我表达的作用,暗示统一制服能防止学生被多变的时尚“分心”。但背后的真正意图(尽管鲜少被承认)则在于将学生塑造成管理者期望的样子——无差异、无特征的个体。
制服对人的约束在以下事实中显而易见:高中毕业后,校服基本上不再是硬性要求,除非是在某些军事或宗教院校。进入大学的那一刻标志着你被鼓励“做自己”的开始,这种自由也体现在着装上,甚至连穿睡裤去上课都变得可接受。不过,大学可能是人生中最后一个能如此随意穿着的阶段。
抹去自我表达的痕迹
一旦步入职场,你将不得不面对各种形式的制服。有些制服是出于功能性需求,比如机械工的工作服;而有些则更多是为了限制你在工作场合的身份,掩盖你的个人特质,使你被工作角色所取代。身穿挂有名牌的Polo衫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喊出我的名字,穿上制服,你既被“匿名化”,又同时被标识化。在制服中,你可以象征性地代表公司,同时个人身份被模糊,从而更容易被他人以非人性化的方式对待。
工作制服和校服一样,都与服从性紧密相连,目的在于抹去任何自我表达的痕迹。只有当一天的工作结束、脱下制服的那一刻,你才能真正感受到回归“真我”的自由。
在企业中,默认的标准制服依然是西装,员工甚至常被称为“西装女/男”。不过,随着美国职场逐渐走向休闲化,以及远程办公人数的持续增长,办公室着装规范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阿曼达·马尔在《大西洋月刊》撰文指出,“千禧世代”已步入管理层,他们对休闲服饰的偏好或将影响职场的整体穿衣文化。她观察到,年轻人“开始用自己的想法重塑‘工作服’的含义,打破了所有人必须遵循单一着装标准的束缚”。
在军队这种等级森严的机构中,金星、横杠和勋章清晰地标示着地位高低;而在相对宽松的工作环境中,等级差异则更为隐蔽。开放式办公室(让首席执行官坐在普通办公桌前、去掉玻璃墙和守门秘书)并不会真的让办公环境变得更平等;低调的穿着同样掩盖不了职场中的微妙差异。大家都穿着帽衫,职场不会因此奇迹般地成公平竞争的场所。
“具衣认知”的力量
初创公司的着装规范,基本只有一个底线:别把自己打扮成“异类”。然而,当科技行业在2020年迎来自己的“烟草巨头时刻”时,这种随意的形象发生了转变。那场听证会上,四大科技巨头领军人——脸书的扎克伯格、亚马逊的贝索斯、苹果的库克和谷歌母公司字母表的皮查伊——纷纷脱下帕洛阿托风格的休闲装,换上灰色或海军蓝的西装,与传统企业和早年商业巨头的高管无异。
在最宽松的环境中,“具衣认知”的力量依然强大。哪怕是那些工作时可以穿紧身裤或睡衣的自由职业者,也常常认为,在工作日换上“正式”服装有助于进入工作状态。类似“为成功而打扮”或“为你想要的工作而打扮”的建议不胜枚举。
通过模仿老板或上司的穿着,似乎能够借助时尚的影响力接近他们的地位。但实际上,在许多公司里,最成功的人反而往往穿着随意,甚至有意无视模糊的办公室着装规范。这本身就是一种彰显权力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