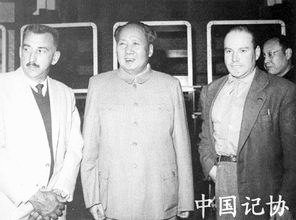

毛泽东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海外学术界对他的研究持续数十年而不止。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毛泽东的研究
1936年6月,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陕甘宁边区,成为第一个访问“红色区域”的外国记者。他根据采访笔录整理完成了《红星照耀中国》(中文译名《西行漫记》)《西行漫记》,书中收有毛泽东的自述:《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成为最早的毛泽东传记。次年10月,这本书在英国伦敦出版发行,之后多次再版。
1948年和1952年,美国历史学家、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和《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1921-1951年》先后出版。在这两部专著中,费正清最早涉及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费正清通过不懈的努力,使毛泽东研究成为专门学问,并创建了早期的专门学术研究机构,培养了一些毛泽东研究专家。
西方发达国家的毛泽东研究的学者中,以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系美籍教授施拉姆、加拿大籍华裔学者陈志让、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史华慈、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德里克、美国政治学家白鲁恂等为代表人物,尽管他们是以西方人的视野来研究毛泽东,但是相关研究成果在这些国家还是起到引领示范的作用。
美英两国是资本主义国家中最早研究毛泽东的,还建立了专门的学术研究机构,学术交流氛围浓烈,并形成了哈佛学派、右翼保守派和新左派。20世纪60至70年代,上述各派还发生过两次论战,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外的毛泽东研究。
日本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介绍毛泽东的文章。全面抗战期间,日本的毛泽东研究有着极其明确的目的性,就是收集中国共产党的情报。抗战胜利后,日本的毛泽东研究才步入学术研究的轨道,其学者多是从毛泽东思想的来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等角度进行研究。
法国的毛泽东研究侧重于毛泽东的生平,相关研究者中不乏著名的学者,如萨特、列斐福尔、阿尔都塞和福柯等。在1968年震惊世界的法国“五月风暴”中,萨特从一开始就支持学生运动,成为法国“毛泽东思想拥护者”的精神导师。
德国的毛泽东研究注重于毛泽东的传记,如扎奇、蒂勒曼·格林、托马斯·沙乐平、彼得·孔策等,都有相关论述。德国的一些学者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颇有兴趣,他们把毛泽东称为20世纪伟大的战略家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英美等国的学者在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时,大多刻意避开或忽略了毛泽东对于当时世界革命和进步运动所产生的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如毛泽东对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美国黑人运动等的大力支持和号召力。这既是西方相关研究的局限,也反映了其本质。
社会主义阵营对毛泽东的研究
苏联是最早研究毛泽东的国家之一,早在1927年6月,共产国际就在其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上发表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34年11月又发表毛泽东的《我们的经济政策》。
1937年至1939年,陆续发表了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和新华日报通讯记者的谈话》《和世界学联代表团的谈话》《论新阶段》《关于国际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等,还刊登了介绍毛泽东等中共领袖的生平及相关评论文章。
《共产国际》上的一系列论著,向国际共产主义者宣传和介绍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为后来学术界的毛泽东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苏联和东欧学者十分重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和军事策略。
他们充分肯定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经验。
南斯拉夫学者M·德鲁罗维奇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和毛泽东的功绩就在于从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出发,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特殊矛盾。毛泽东不是导师或‘天生的哲学家’,而是始终置身于与世界上任何革命运动都不相同的中国革命斗争中,他的著作反映了中国革命实践的策略思想。”南斯拉夫学者P·费兰茨基对毛泽东哲学著作也有评价,认为毛泽东是杰出的辩证法家和革命策略家。
备受推崇的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讲话中指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精彩的论述是国外研究学者最欣赏和认可的部分之一。
土耳其裔美国著名学者阿里夫·德里克认为,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使“马克思主义具体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的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视野出发对中国社会的反思,而且是从中国作为一个第三世界社会和民族出发而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
斯洛文尼亚作家、学者斯拉沃热·齐泽克是著名的毛泽东思想研究专家,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有过两次重大传承重大改造:一次是马克思到列宁的传承和改造,一次是列宁到毛泽东的传承和改造。他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第二次重大改造。
海外学界在研究毛泽东《矛盾论》《实践论》时,普遍认为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哲学。在中国革命早期阶段,列宁主义比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的影响更早更大,依据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列宁主义的照搬。莱文认为,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进程中意识到中国革命不同于俄国革命,所以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毛泽东还运用马克思和列宁没有用过的方法来提炼矛盾的概念。”
毛泽东文献在海外的出版
20世纪70年代,日本毛泽东文献资料研究会开始收集出版毛泽东的著作,由被誉为日本“毛泽东学”权威和“现代中国研究第一人”的竹内实具体负责。竹内实主编了《毛泽东集》10卷、《毛泽东集·补卷》9卷及别卷,共20卷,并以简体汉字出版。这个文集现已成为国外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的重要资料。
施拉姆是海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的权威,在文献考证和版本研究方面的成就,一直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可。他最早完成的《毛泽东政治思想》《毛泽东》,在史料的收集上尤为详实。1989年,施拉姆退休后即被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聘请,主持编辑大型英文版毛泽东文集《毛泽东通向权力的道路1912-1949》。施拉姆还编辑了《未经修饰的毛泽东:谈话与书信集(1956-1971)》。
美国学者史华慈、加拿大学者陈志让、德国学者马丁等都投入了毛泽东文献的收集和编辑工作,并都出版了文集。 (摘自《文史精华》2023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