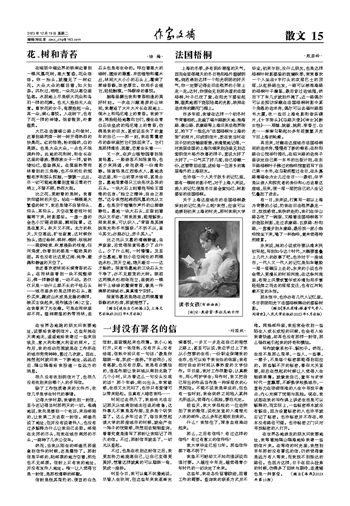在世界各地跑的朋友问我要地址,说要给我寄明信片。这些年她在天南地北,遥遥地给我寄过一些来自埃及、意大利和澳大利亚的照片。工作后,我的活动范围就是在工作所在的城市兜兜转转,搬过几次家。因此,她想起时就问我一下新地址,远远近近、隔山隔海给我投递一些远方的消息。
很久没有收到明信片了,也很久没有收到来自哪个人的手写信。
除了工作性质寄来的文件外,收信几乎是学生时代的事情。
记得大学时期,我曾收到一封信,至今还记得当时那两天的一切。准确地说,我先是接到一个电话,来自邮局的,让我第二天去取一封信。邮递员说了地址,但并没有说寄件人,也没有过多解释为什么让我自己去取。邮局在北郊的尽头,而我在城市南郊的尽头,一路转了几次公交车。
然而,当我从陌生的邮递员那里拿到信件的时候,还是震惊了。那封信是平邮的,贴邮票的地方空着,别处也不见邮票。信封上只有我的地址,并没有发件人地址。唯一让人觉得它是一封信,是那枚清晰的邮戳。
信封是极其简约的、便宜的白色信封,里面摸起来也很薄。我小心地打开,只有一张信纸,没有开头,没有结尾,信纸中间只有一句话:“最是你眉眼一弯,笑成一座桥。”字迹很小,没有落款,也没有日期。我是有点懊恼的,谁恶作剧让我环城从南到北跑了几个小时,只为看这么一句没头没尾的话?那个年龄,刚20出头,非常敏感,生活又太沉闷了,也许只有爱情可以带来轻松。当真有人暗恋我吗……
时间过去很久了,我始终无法忘记那天从城南到城北往返的疲惫,这件事儿不算是恶作剧,至多是个玩笑罢了。这么多年过去了,每当我想起读大学的那座城市的时候,就会产生一阵子的恍惚感,很想回去细细查询,看看究竟是谁写了那封让我惦记了很久的信。不过,那封信早就丢了,一切无从查起。
不过,也是在收到这封信之后,我更加努力地提高自己,让自己变得更美好,想着这样就真的可以眉眼一弯,笑成一座桥。
时至今日,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尽管人生坎坷,但这些年来我逐渐充满喜悦,一步又一步走在自己的理想之路上,甚至可以说,我近乎过上了我从小想要的生活:一份职业保障我的生存,也可以给予我世俗的体面;我有相对自由的时间从事热爱的文学创作。平日里,我对工作很勤奋,认真教书,用心呵护学生;写作时,我又把自己写出的作品当作是一种深层次的心灵探险。不能不说我是幸运的,但也有一些时刻,我会突然之间陷入某种无所适从,觉得内心孤独,漂泊无定。
前些天,我大学母校的一位老师加了我的微信,说收发室的人清理无人收的邮件,这么多年还能收到我的。
什么?我惊住了,浑身血液涌动起来。
那么,之后有信吗?有过这样的信吗?有过有意义的信件吗?
我大学毕业已经12年。那些信件都下落不明了?
我急不可耐却又不知向谁诉说向谁讨要。人越往中年走,越觉得青少年时代的一切决定了未来。
这些年,我在各处留着踪迹,因着工作的需要。查询我的联系方式并不难。网络邮件里,我经常会收到一些陌生人或长或短的问候,也会有人给我寄快递,却再也没有那样一封信,那么强烈地引起我的好奇和懊恼。
写作就像系扣子、解扣子。然而,生活不是那么简单,一些人,一些事,一辈子,不是每个秘密都能得到回应的。那些解不开的秘密,看似无关紧要,却总在想起的时候让人觉得人生细碎单薄。就像我自己,童年与求学时代一直飘零,不断换学校换城市,一直努力在琐碎艰难的人生中寻找平衡点,内心充满了恍惚与孤独。现在,我试图在我的写作课上讲述生活是可以解释的,而实际上,一些秘密根本就没有解法,因为设置秘密的人也许早就忘记了秘密。也许秘密并不存在,根本没有路径可循。也许秘密之门只对寻找秘密的人打开。
在世界各地游走的朋友问我要地址,我等着她隔山隔海地给我寄一些明信片来。在等待的时光里,我想到早年那封没有署名的信,仍然觉得像是远方有人等我,而我找不到抵达的路径。也因为这样,日子在回头检索的时候,仿佛多了回味与期待,连遗憾也是一种享受。 (摘自《海燕》202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