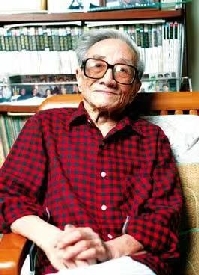
说实在话,从小到大,无论是哥哥还是我,与父亲范用交流并不多。我们小的时候,他整天都忙,顾不上和我们说什么,就连喝酒、吃饭的时候也常是边喝、边吃、边看书看报,不怎么理睬我们。等到退休,不那么忙了,他喜欢一个人看书、看电视、喝酒,吃饭也经常与家里人不同步,就像我女儿上小学时在一篇日记中写的,“我们吃饭的时候他睡觉,我们睡觉的时候他吃饭”。
记忆中,父亲和母亲对我们的学业很少过问,顶多是学期末看一看成绩册,即便哪门功课成绩不大好,也未见很着急。不过父亲对我们的成长并非不关心。记得上小学之前,每晚睡在床上,父亲都会给我讲一段《格林童话》或是《安徒生童话》中的故事。他还给我订了《小朋友》和《儿童画报》两份杂志。这两份杂志成了我和小伙伴们共同的精神食粮。
20世纪60年代初,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一则有关毛泽东主席畅游长江的报道,激起一场全国上下学游泳的热潮。父亲在那个时候学会了游泳。接着他就兴致勃勃地教我游泳。那年暑假里,他先是让我在家把脸泡在脸盆的水里学憋气、吐气,然后又利用每天午休的时间,带我到工人体育场游泳池教我游泳。就这样,这个假期里我也学会了游泳。
1968年,我下乡去了黑龙江农场。那时父亲的来信中有时还夹带着先前我写给他和母亲的信,里面的错别字和病句都京被他标出并做了修正。
父亲爱书,家里书架、书柜上的书,都是他一手摆放的,哪本书在哪里他非常清楚。如果发现有人动过他的书,就会追问。他倒不是反对我们看书,只是担心书被弄坏、弄脏。
除了爱书,父亲还有很多喜好,例如,看电影、听音乐、吹口哨、收集有趣可爱的小玩意儿、养金鱼、做爱吃的小菜、种花草、集火花(火柴盒上的贴画)。走在路上,他嘴里时常吹着歌曲。他曾收集了几大本火花,有时还与其他火花爱好者通信交换各自多余的品种。
父亲喜爱孩子,见到小孩子他就很开心。1981年我的女儿出生,产后最初两个月住在父母家,父亲时常抱着我女儿哄逗。父亲不喜欢体育活动,但是他喜欢看足球比赛。退休后,每逢足球世界杯赛,他会守在电视前整夜地看。其实他并不懂足球比赛,只要看到进球就大声叫好,也不管进球的是哪一方。
父亲的很多朋友说父亲慷慨好客。他有时给报刊投稿,文章刊登后能得到点稿费,每次拿到稿费,他就请上几个老朋友或是小朋友,找家小馆子一起吃顿饭。
母亲有位侄女,从江苏远嫁到广西,生活不宽裕,母亲生前每到过春节会寄些钱给她。2000年母亲去世后,每年春节,父亲都替母亲继续寄钱去。
父亲的单位每年最后一个月都给职工发双份工资,父亲对家里雇用的保姆也实行这个政策。有一年他到香港去访问,回来时给家里每个人都带了份礼物,其中也有买给保姆的毛线衣。
从这些事看,父亲是慷慨的。但是对家里人,他有时又小器得很,一些吃的、用的东西,喜欢独自享用,不让别人碰。与父亲相处时间不长的人都说他是个和气、幽默的老头。但是家里人却感到他脾气大,急躁,任性,固执。我们有时当着母亲抱怨父亲脾气不好,母亲总是说:“他这个人像个小孩子,别跟他计较。”
1994年父母搬到方庄居住时,都已是70多岁的老人,为了避免休息时互相干扰,他们各住一间卧室。母亲去世后,按照父亲的安排,母亲的骨灰瓶存放在她生前的卧室中,父亲也住进这间卧室,伴着母亲的骨灰度过了生命的后十年。 (摘自《博览群书》2024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