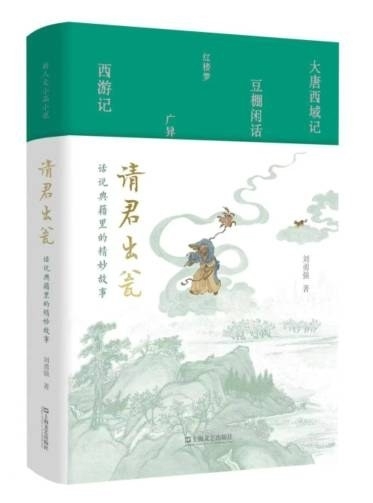
《请君出瓮:话说典籍里的精妙故事》 刘勇强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年8月出版
本书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刘勇强教授的一部新人文小品小说集,收录了近五十篇取材于古代典籍和文献资料的新编小说。书中着意化用古代小说的语言乃至诗文的佳篇警句,旧瓶装新酒,夺胎换骨,激活古代小说的艺术生命。
这几年,我写了些所谓新人文小品小说,在接受一个采访时,我声称是“趣务正业”。这虽是为自己的以文为戏张本,但多少也合乎实情。本书的《灯》一篇写于2009年,取材于《阅微草堂笔记》;另一篇《脚步》是因了与学生的“西游记读书会”;《子孙果盒》《清凉》与“儒林外史读书会”有关,《魂无所依》与“聊斋读书会”有关。往大里说,所有的作品又都与我一直从事的古代小说研究有关。在阅读古代小说时,我常为一些作品精巧的构思与深刻的内涵打动,便产生了光大弘扬、推而广之的愿望。这是我写作的初衷。
南京大学苗怀明教授创办“古代小说网”公众号之初,向我约稿,我先呈旧作,后逐月写作一篇,请他发布。每次怀明兄都精心排版,及时发布。推出后,又得到不少朋友的跟帖评点、打赏、指正。及时的反馈,既有用心处被留意的兴奋,也有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反应令我好奇,都成为我写作的一个重要动力。我要特别感谢的是现在美国大学任教的徐芃女史,有一次她在转发时,用了“新人文小品小说”雅称,我当即回复表示要“笑纳”,因为我觉得这一称谓恰到好处地概括了我的旨趣。
古代小说从来就不只是过去时代的文学遗产。我的基本意图就是,努力揭示古代小说文本中蕴含的情感、思想、审美元素,通过旧瓶装新酒,夺胎换骨,激活古代小说的艺术生命,使之与今人的观念、趣味相呼应。
实际上,不断翻新也是古代小说的传统,比如唐代有一篇小说《郭翰》,写的是织女从天而降,与郭翰共成夫妇之好。唐代小说家竟让这个美丽神话的女主角私奔,实在是惊人之笔。这种顺应自然天性、向往人间生活的描写,看上去是对神话文本的解构与反叛,但从本质上说,它又是与神话所传达的自由精神一脉相承的。类似这样的写作,在古代小说中不计其数,大量的话本小说就是依据之前的文言小说翻新创作的。清代小说《豆棚闲话》对本事的颠覆性改编,更赋予了经典文学形象崭新的人文意义。文本的代代相续、不断翻新,可以说构成了古代小说一种互文性传统,使得古代小说成为国民情感之流绵延不绝的印证。
如果放开眼界,翻新创作也是一种宽广悠久的文学传统。近代文化转型期,就出现了一股对古代小说翻新写作的潮流。鲁迅的《故事新编》则是现代小说家翻新之作的经典。当代作家中,汪曾祺、刘以鬯等,都有这方面的佳作,刘以鬯的《蛇》对《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的改编,就是我特别欣赏的优秀作品。日本作家中岛敦《山月记》对唐人小说《人虎传》的改编,也堪称精品。
前些时候翻阅彼得·阿克罗伊德的《狄更斯传》,其中论及狄更斯借用其他作家的艺术效果、人物和情节时说:“狄更斯抄袭或借用的素材,根本比不上他将其转变成自己独特艺术组成部分时所依据的原则来得重要。对他来说,这些片段是灵感的来源,他缩写、扩充、改编这些片段,但在任何情况下原始素材都只是因为其在狄更斯小说中的全新搭配组合才具有意义。”这样看来,翻新可能还是一种世界文学的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