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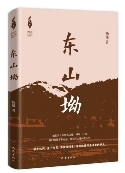
(《东山坳》,作家出版社2024年8月出版)
开始我还不太相信,后来听着看着,我就坚信不疑了。
大青马站住后,人们像水波一样围了一圈儿又一圈儿。尚大祥拎着鞭子,眼珠血红,扯着喉咙嗷嗷叫骂:“畜生!我宰了你!”手里的鞭子却无法甩起。他被人们箍住了。人们开始数落大青马,说它丧良心,活活把拿它当眼珠子的尚全有踢死了。数落声像河水决堤,漫过东山坳,淹没了大青马。它怵怵地站着,灰白的身子不住颤抖。
我和韩松花般般儿大,那之前我眼里看不出美丑。那之后,经过与同村女孩儿比较,我相信了人们的说法:大青马是被韩松花的脸蛋儿给镇住的。
那时候,人们说起她那张脸蛋儿,经常是以一声“哎呀”起个头,我到现在还能绘声绘色地学出来——
“哎呀,咱村松花,不会是七仙女儿托生到老韩家了吧?”
“哎呀你说,松花那眼睛咋长的?水灵灵两颗大葡萄。那对小酒窝儿,王母娘娘跑她妈肚儿里给画的吧?”
人们总这么说,韩松花在我眼里就好看起来。韩松花一好看,我见到她就开始越来越别扭。
韩屯小学在村边儿上,我们这拨孩子每天都要穿过小石河才到学校。那阵子不管在学校、在路上,尤其是在小石河的那座小桥上,每次见到韩松花,我都像撞见了恶魔。我的脸比木头还僵硬,腿脚比桥柱子还强直,气哼哼地从她身边飞跑过去。
郑四方认为我得了神经病。连那么懦弱的家伙都这样说,我也对自己产生了怀疑。有一天,放学路上没有韩松花,我用最交心也最狐疑的语气问郑四方:“你说,好看吗,咱村那个韩松花?”郑四方用不确定的眼神看着我,我在他的眼神里看到了我问话时的眼神。我的好朋友郑四方思索片刻,以一个三年级男生的诚恳对我说:“你回去,问问你爸妈,我回去,也问问我爸,还有我妈。”
铁匠爷爷说过,郑四方他妈把他生早了,他就该一直待在他妈肚子里。
“问完,明天俺俩碰一碰,就知道好不好看了。”
我觉得郑四方的神经病比我重,就不服气地问他:“为啥说我神经病?”
“跟我妈学的。”
“你妈?说我呀?”
“说我爸,她说我爸神经病。”
这就对了。村里谁不在背后说郑万山不着调啊。这个人有副闲不住的腿脚,除了种地,天底下好像没有他不爱干的事儿。原先,他最爱给黄皮子、野兔子下套,一张皮剥下来,连着那生灵的小头颅,能卖好几块钱。生产队解散后他就挨家挨户收细参、穿龙骨这类药材,也收松子榛子核桃这些山里的坚果,再拿去城里卖掉。说他没钱,村里数他穿得人模狗样。说他有钱,郑四方那几块钱学费他都掏不出来。后来知道他每次进城为啥一待就是好几天了,是认识了一个收山货的女人,那熙熙攘攘光天化日的地方,俩人就好上了。城里离韩屯上百里,口风原本传不过来。可郑万山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经常半夜紧闭双眼,像当年高呼口号一样高喊那女人的小名儿——蝶儿,小蝶儿。郑婶儿跟婆娘们学了,都说她男人身子肯定是丢了。郑婶儿信了,又不愿信,眼神儿变得直直的。她男人嫌弃她五大三粗,尤其厌烦她那双四十码大脚。她就家里外面地说,她男人得了神经病。我们村有个不成文的认识:神经病干啥都不是故意的,只要得了神经病,干啥都不犯法。郑婶儿说她男人神经病,是寄希望于她男人不是故意失身的。郑四方说我是神经病,就万万没道理了。我宁可变成女的也不想成为郑万山,于是我带着小学三年级男生特有的固执继续强调:“我不是神经病。”
郑四方从生下来就睡小米枕头,后脑勺彻底消灭了头骨的弧度,长得像块方方正正的砖头。我目睹着一块方砖是怎样烧成红色,作为班里唯一离开学校还扎红领巾的男生,比我大三个月的发小,终于磕磕巴巴地说出他眼中我的病根儿。
“平时……没病,见到韩松花……不是跑就是瞪,就来病啦……”
“我没有——”
“我爸,见到我妈,跟你一样,不是跑就是瞪……”
那时候,我完全没意识到自己正拥有着世上最宝贵的东西,长大后我才知道那种东西被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定义为纯粹的友谊。以此推断,我也曾是个最纯粹的朋友——每次我说郑四方是缩头乌龟、胆小鬼,都是张口就来,绝不会思前想后,更不会把心里的话打个漂亮的包装,再作为礼品送出去。纯粹的友谊让我再不能用神经病的方式面对韩松花,我确实就像变了个人。
我首先承认了韩松花好看。
四年级的作文课上,语文老师把韩松花叫到黑板前,不让她坐凳子,必须保持站姿一节课。韩松花成了那节课的题目,每个人都要写一篇三百到五百字的韩松花。第二天,语文老师手拿三十余篇韩松花,面色既高兴又凝重,对全班说:“我敢保证,这是咱班真实水平,谁也没抄谁的。”我相信听到这里,连倒数第一都会感受到学习生涯的第一次鼓舞。老师又继续说道:“谁也没抄谁的,还能写得一模一样,你们老师我,感到挺惭愧。”
当年的这个奇迹是这样两行字:韩松花有双铜铃般的大眼睛,一对活灵活现的小酒窝儿,还有一张粉扑扑的小脸蛋儿。这句话被三十份作文写了三十次。它的出处正是老师的嘴。老师教我们怎样抓住人物特点,指着韩松花的脸这样描述了一番。
我也是这么写的。我这么写是因为我对此毫无异议。我这么写是我当着全班承认了韩松花好看。没想到,承认之后我要面临的,却是更大的难题。
要知道,当时在农村,没人对我们进行过美育教育。相比之下,我们天生就知道怎样面对恶、坏、饥寒甚至传说的妖魔鬼怪,就是不知道怎么面对好看。孙悟空见到好看的就打,这多少也让我看到了村里人对待好看的态度。村北面有个三十多岁的寡妇,大伙儿都说模样挺俊俏。我也常见到,不明白那尖下颏儿、吊眼梢儿、杨柳细腰是不是真俊俏,只知道全村女人都叫她骚狐狸,我就只管见她就躲。韩松花是小姑娘,自然没人那样说她。可韩松花毕竟是“好看”,“好看”就像一个特殊的物种,把我难住了。
我总是躲着她。那时候我不知道世界上曾有个叫歌德的人,为了一个叫绿蒂的姑娘,献出饱蘸情意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如果我当时有幸知道,一定会羡慕少年维特,至少他知道自己喜欢绿蒂。我什么都不知道。甚至我一边躲着一道叫“好看”的难题,一边整日寻找这道难题的漏洞。我想找出韩松花的毛病,能让我像面对邪恶和坏蛋一样,划清界限,嗤之以鼻,继而抛之脑后。
一个寻找漏洞——俗称找毛病的人,往往无须扬鞭自奋蹄,往往对此有着无穷的精力。但是请相信,我的找毛病没有任何恶意,我不过是想让自己面对好看能坦然,能不再手脚无措,能像不知好看为何物时一样,无忧无虑。
(选载之十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