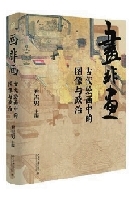
《画非画:古代绘画中的图像与政治》
尹吉男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1月出版

艺术史研究能否超越学科的边界,为更广泛的人文社科研究提供启发?艺术史中的经典作为历史的图像遗存,是否还隐藏了更多的信息?而今天的我们又是用什么样的方式破解图像密码,了解到这些隐秘的政治与历史信息的……本书汇集了艺术史研究中的一系列经典研究成果,回答了这些问题。
在上海博物馆所藏元代名画中,有一卷题为赵孟頫所绘的《百尺梧桐轩图》(见图)。此图绢本,青绿设色,画的是园居闲适之景。图中一人便服闲坐在精雅的草顶轩堂中;左侧廊中一个披发童子捧茗,堂四周高桐环绕,间以桂树和竹林;右侧水边有一个侍者抱琴而来。全图笔法秀雅,设色工丽,在传世元代绘画中堪称佳作。画后有元代周伯琦、张绅、倪瓒、宇文材、饶介、王蒙、马玉麟七人题诗,都是元末名家。
1985年全国书画鉴定组在上海工作期间,笔者初睹此图真迹。在欣赏其精雅之余,也发现画幅右上方的一行“吴兴赵孟頫”款识笔法滞涩,徒存轮廓,画幅右方也颇显局促。笔者反复分析,认为它是一幅被人裁去原款又补加伪赵孟頫款的元人作品。画后七人的题诗都是真迹,且所咏与画意相符,为原跋无疑。从诗意看,此图是替一个曾为宰相的人画的园居行乐图。当时任务紧迫,匆匆一览而过,无暇详细研讨,但对绘画之精雅、题诗诸人声名之烜赫,留有深刻的印象。
鉴定组工作结束,偶然翻阅旧札记,对题诗内容和诗人题诗的时地略加考订,意外地发现,此图虽非出自赵孟頫之笔,但也有很特殊的历史艺术价值。
由于画上赵孟頫款为伪加,原题款已佚,画后题诗也没有上款,我们只能根据题诗的时间、地点、内容逐步缩小范围,以考订此图的主人公是何人。
综合分析,笔者认为根据诸人题诗内容和当时历史情况,这幅画所绘是张士信园居的图景,堂中独坐的就是张士信。从现有题诗都出自当时名家和画本身的精工秀雅来看,此图作者应是当时居留在平江的名画家。其画风在继承赵孟頫的同时,也似受盛懋的影响。此图之所以被裁去原款,笔者以为是当时的收藏者为了把它保存下来,不得不掩盖它与张士信的关系所致。
张士诚是泰州盐贩出身,兄弟四人,起事以后始取名为士诚、士义、士德、士信。士义至正十三年初起事即战死,士德在至正十七年被朱元璋军俘获而死。到张士诚割据平江建立政权时,只有四弟张士信尚存。张士信在张氏政权开拓和巩固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先后率军或指挥诸将攻占杭州、嘉兴、湖州、绍兴等地,平定淮南之叛,攻刘福通、韩林儿等,屡立战功。后为太尉、丞相,封为“国弟”“太弟”,具有张士诚继承人的身份,是仅次于张士诚的最有权势人物。
在元末群雄中,堪为朱元璋劲敌的是陈友谅和张士诚,尤以张士诚为腹心之患。张士诚失败后,其重要臣僚除事先投降者外,大部被杀,入明后,对曾和张氏政权有联系的文士尤存猜忌,陆续以种种手段加以杀戮或迫其自杀。有关张士诚据平江时的史料,除官方销毁外,藏之私家者,也大都因畏祸而自行毁改。
为研究此图,笔者曾翻检明卢熊撰(洪武)《苏州府志》和明王鏊纂修(正徳)《姑苏志》,在二志中,关于张士诚据平江时的史料几乎无一言。显然,对卢熊来说,如果当时不是有大不得已之处,是不会噤口不言的;而对《姑苏志》的作者们来说,则是史实湮灭,欲书不能了。从这些情况可知在明洪武间对这些事避忌之深和禁遏之严。故此图之截去原款,补加赵孟頫款,实是出于保存的目的而不是作伪欺人。
不仅此图本身遭到裁割,笔者颇疑图后现存的七人题诗也是裁割之余。现存七人题诗高低不同,张绅、倪瓒、饶介、王蒙四人都充幅书写,上下没有多少隙地,而周伯琦、宇文材、马玉麟三人所书则天地头都留存较宽的余纸、格式不一、错杂连缀。其中倪琳诗题于至正二十五年七月,反倒位于同年六月饶介题诗之前,次序不顺。从这些情形看,极可能原来题跋者尚多,那些有上款或词意明显无法掩盖此图与张士信的关系的已被撤毁,只保留下这七人之诗。
张士诚以平江为中心,建立政权,割据江浙地区达11年之久。在此期间,大量著名的文士、诗人、书画家,或求官,或避乱,聚集在富庶而相对平静的平江,在张氏政权的优待宽容下,得以诗酒流连,征书索画,创作了大量的诗文和书画作品,在遍布全国的起义烽烟中,形成一个文学艺术独盛的孤岛。尽管从形势发展看,这些人可谓燕巢于幕,鱼游釜底,但其作品毕竟是元末文艺的一个重要方面,并直接影响明初。由于明初对张士诚政权史事的禁遏,很多流传下来的作品都掩盖其创作的历史环境,特别是与张氏政权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