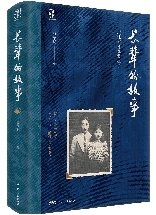
熊景明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2025年1月出版

1939年,四世同堂,长须老人就是曾祖父,手扶拐杖的幼童是我的哥哥,摄于昆明大观楼
本书是一部家族记忆史,透过人物的命运沉浮,展现了昆明自民国至共和国近百年的风云变幻和新旧冲突,以及时代风暴对一个大家庭的影响,细腻地描绘了在时代巨变的潮流中,一群普通人是如何恪守传统美德,坚守人性的美好信念,以至情至性温暖彼此。
曾祖父熊廷权(1866-1941),这位道尹大人听起来像一位可爱的老翁,养着两只小狗,留意花瓶要不要添水,分享农人丰收的喜悦。拿本书斜躺着最觉自在,吟诗作对求惊人句。此官生活简朴,出门不着官服,不车不马,独自串田家,居然贪看秋花忘路远。有过疆场厮杀马上驰骋的经历,冷眼看官场,暗自嘲笑无事忙的同僚、部下。
最大考验
按当时必须异地做官的制度,熊廷权被派往四川高县任县长。三十出头的人彼时做县长稀疏平常。他“初补高县,调补营山县、富顺县,历署彭县、庆符县。卓著政声,迭奉传旨嘉奖,保升知府”,在任上先后受过清廷三次传旨嘉奖,估计其中一次与在富顺县镇压哥老会的武装起义(1908-1910)有关。起义由同盟会的熊克武连同当地袍哥组织发起,熊克武是辛亥革命先驱,很得蔡锷赏识,其中矛盾需要历史学者去解读。曾祖父留下的著作中仅有一篇《创建高州小学堂记》和这一时期施政有关。
在四川任职期间,年轻的县官经受了毕生最大的考验。1905-1907年两度出关,以参军事的身份到西藏东部办理粮务,负责当时到西藏镇压叛乱的清军之后勤,输送粮草。100多年前进藏的艰辛,如今难以想象。“于冰天雪地艰难困苦中,疏通运道,接济军需”,可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藏东边坝县丹达山有一块石碑,记载了1753年奉命率部队运粮食到西藏的云南参军彭元辰的事迹。队伍途经丹达山时,遇大雪封山,被困于悬崖边。无计可施,这位参军纵身跳下雪海以身殉职。负有同样军令的熊廷权,在同样的天气中在同一条路上走过。
进藏平叛
五年后,已经在丽江知府任上的熊廷权临危受命,再与西藏结缘,重拾参军事的职位,辅佐当时滇军将领殷承进藏平叛。民国初建,尚在风雨飘摇之中,武昌起义后,驻藏川军树起“大汉革命”的旗帜,行迹如土匪。十三世达赖在英印总督支持下发表《告民众书》,要将汉人驱逐出境。四川都督尹昌衡亲自带兵进藏,试图收复被西藏民军占领的地盘。滇军千里入藏,夺回重地巴塘,之后奉命撤回。
这一段历史,英国人、藏人、川军、滇军,各自有不同的说法,说的都是军事和政治,并未涉及战争的惨烈,看不到官兵、民众的困苦和牺牲。千辛万苦的西征,无功而还。熊廷权写下长文《乌斯藏哀词》,刻为碑文,至今仍立在丽江黑龙潭边山坡上。文章为士兵鸣不平,为支付战争开支的民众鸣不平:
……朝下一令曰其速来,暮下一令曰其速去。岂计及我昆弟子侄之生命牺牲几何,我伯姊诸姑之簪珥损失几何乎!今亦既班师矣!风云帐下,磨残烈士壮心;鼓角镫前,洒尽英雄老泪!……
三度以军官身份入藏,影响熊廷权的一生。西征的滇军将领殷承与熊廷权同赴沙场,与他“相从日深,知其才大而性傲,觥觥以名节自重。昆明人士多柔靡,而君独翘然名重一时”。他们从藏人手中收复了战略要地巴塘,自己则被西藏的文化宗教所征服。殷承不久退出军政舞台,专心研究藏传佛教。曾祖父写下《西藏旅行日记》《西藏宗教源流考》(均已失传)。他从西藏带回《大藏经》,后人捐给云南省图书馆。
至交蔡锷
云南晚清的官派留日学生达300多人,大多习军学政。熊廷权的几位好友都赴日学习,包括李根源和后来结为亲家的钱用中等。革命者摇旗呐喊,唤起年轻人心中激情,云南的留日学生中绝大多数人都参加了孙中山发起的同盟会。
作为晚清进士、官员的熊廷权也不例外,他热情地拥护变革,和蔡锷成为至交,受其委派出任川边道尹兼财政厅厅长。护国运动时,他曾抱病去见蔡锷,“一夕洽商,疑难尽决,兵不血刃入成都”,也曾写下《为护国各军自总司令以下阵亡病故诸先烈招魂词》:
边风起兮关山长,阵云冷兮压嵩邙。天沉沉兮塞草黄, 雪霏霏兮日霾光。万山寂寂兮河水泱泱,番马怨鸣兮声凄凉。 通帝谓兮告巫阳,试披发兮下金阊。天苍苍兮地茫茫,魂之招兮自何方?北河湟兮南衡湘,西流沙兮东扶桑,归来归来兮勿徬徨……
1916年12月1日,熊廷权与殷承联名写下《祭护国军总司令邵阳蔡公松坡文》。
民国成立,对熊廷权一家而言,最大的好处是取消了官员不得在本省任职的规定。他终于回了云南,成为第一任丽江知府。来到滇西这片以纳西族为主的美丽土地时,熊廷权已经是一位行政经验丰富、经过战火洗礼的官员。丽江三年公职令他得以施展抱负,有所建树,为百姓爱戴、感念。
1990年代初,我参加新西兰一个农业技术援助项目,从香港来到丽江。说起80年前曾祖父曾到这里做官,出乎意料,当地不少人都听说过他的事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