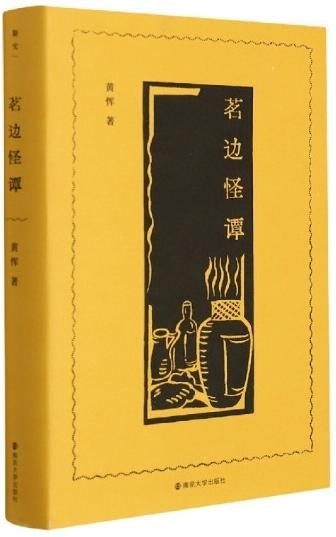
(摘自《茗边怪谭》,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2月出版)
高伯雨《听雨楼随笔》(牛津版)第五卷有一篇《怀安街可怀乎?》,谈到胡适在上海吃花酒的事:
民国十年(1921),胡适乘北大放暑假之便,到上海玩一两个月(其实是商务印书局要革新,坚请他担任编译所所长。他特地来上海观察一番的。结果他推荐王云五)。某日,上海的小型三日刊《晶报》登出一段有趣的消息,说的是《胡圣人吃花酒》。一经传开了,立即成为上海人茶余酒后的材料,原来圣人也吃花酒,吾辈非圣人,到花丛随喜随喜,更振振有词了。
《晶报》并非造谣,的确是有人亲见胡适某夕在四马路会乐里某某书寓吃花酒。《晶报》揭出后,胡博士没有告他毁谤名誉,亦以当时吃花酒实为一种“高级娱乐”,为社会所公认。
然而,高伯雨写掌故太想当然了。当我循着他的指引翻遍1921年的《晶报》后,才知道他的说法不确,因为《晶报》这一年并没有如是或类似的报道。这一年胡适确实到过上海,也就是他推荐王云五入职商务印书馆的那段时间。
《晶报》报道胡适吃花酒,其实是在1926年3月(这一年胡适才36岁),题目是《胡适之底吃花酒尝试》(骚胡投稿):
胡适之先生,自从剃去了胡子以后,居然是个小白脸了。他本来是翩翩年少,不知什么人,加着他一个圣人的徽号,不免有些陈腐气。其实胡先生虽然自称为徽骆驼,我们瞧他是风流蕴藉,兼而有之。昨天有人报告说是胡适之先生,阴历正月十六那一天,在同春坊沿马路宝蟾家,请人家吃花酒。他老先生自己做主人。有人说:京戏里有一出宝蟾送酒,胡先生难道要做薛二爷吗?有位朋友道:不对,薛二爷是反对宝蟾的,这或者是薛大爷吧。其实薛大爷还是胡适之先生做白话诗的老前辈,你们不曾读过《红楼梦》上的:一个蚊虫哼哼哼,两个苍蝇嗡嗡嗡吗?听说那位姑娘,本在生吉里,唤作舜琴老三,便由生吉里调到同春沿(引者按:同春里沿马路的简称),改名为宝蟾老三。第一天进场,胡适之先生便答应给她做花头,摆了一个双台,房中有一副金字的对联,上联是“此日未足惜”,下联是“开尊对瑶华”。据说这位宝蟾姑娘,小名就唤作惜华。这副对也是胡适之先生的大作,对联上的末一字,嵌了惜华两字。不过这件事,尚待考证。就这副对联看来,似对非对,很有些新文化的意味咧。据我们知道,胡先生正为某一家书坊,把一部《海上花列传》加新符号,做考证。上海吃花酒的事,更非加以实验不可,研究社会学的学者,各处都要走走,所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一次大概是胡适之先生的吃花酒尝试了。
附告一句:这位宝蟾姑娘,是个松江人,鹅蛋脸,双眼皮,非常(引者注:旧报原文缺失两字,疑为“漂亮”)。你们不信,请叫来看看,可见胡适之先生的眼力不差咧。(1926年3月6日《晶报》第三版)
20世纪20年代,上海的妓界还是延续着固有的规矩,即客人答应给妓女做花头,必须经过几个步骤。首先是介绍认识,有朋友介绍或自己到书寓里打茶围,然后在酒楼喝酒的时候飞笺叫妓女出堂差,一来一去熟悉之后,就可以到这个妓女的房里碰和(打牌)或摆台(请客),考究一点,就是摆个双台,这是给自己认可的妓女挣面子的事,就是所谓做花头。
胡适给宝蟾老三做花头,已经到了摆双台阶段,可见来往也非一时了。难怪这位以前叫惜华,又叫舜琴老三的宝蟾老三的房中还有胡适送的嵌名对。胡适这次到上海,原是到亚东图书馆给他的徽州同乡汪原放做小说考证的。汪原放标点旧小说,胡适就为新式标点的旧小说如《水浒》《红楼梦》《海上花列传》等做考证和写序文,两人协作,也算整理国故的一个部分。所以这位骚胡打趣说:“上海吃花酒的事,更非加以实验不可,研究社会学的学者,各处都要走走,所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一次大概是胡适之先生的吃花酒尝试了。”
该文对胡适打趣调侃得很厉害,是《晶报》典型的风格,并不算离谱,胡适见了也不好说什么。文章里面提到了吃花酒、胡圣人等等,应该就是高伯雨所谈意中的那篇文章,只是他记错了因果和日期,过于想当然了。
张丹翁在《上海画报》有一首《捧圣》谐诗,写胡适道:
多年不捧圣人胡, 老友宁真怪我无?大道微闻到东北, 贤豪哪个不欢呼?梅生见面常谈你, 小曼开筵懒请吾。
梅生,摄影家黄梅生也,好谈胡适掌故;小曼即大家熟知的陆小曼也。此诗可以窥见胡适与上海小报文人之间的亲密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