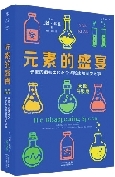
(摘自 杨蓓 阳曦译《元素的盛宴》,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22年7月出版)
自古以来,医生就用木头做成笨拙的假肢,取代人身上缺失的肢体。工业革命以来,金属假体渐渐普及,“二战”后有的残疾士兵甚至用上了可拆卸的锡脸——这样的面罩让士兵能够穿过拥挤的人群而不会引来太多注目。理想的解决方案是让金属或木头和身体融合在一起,但没人做得到。
20世纪90年代早期,我妈妈移植的髋关节是钛制成的。我妈妈运气不太好,她很年轻的时候髋部软骨就因关节炎而磨损殆尽,只剩下骨头吱吱嘎嘎地相互摩擦。35岁时,她做了全髋关节置换术,这意味着将一根一头有个球的钛钉像铁路枕木一样敲进锯掉了一部分的股骨里,然后把关节窝拧到骨盆上。几个月后,妈妈多年来第一次在走路时摆脱了疼痛的困扰。
不幸的是,还不到9年,她第一次移植的髋关节就出了毛病。疼痛和炎症卷土重来,另一组外科医生不得不再次给她开刀。结果显示,假的髋关节窝里一些塑料元件开始脱落了,妈妈是在梅奥诊所做过两次髋关节置换术的最年轻的病人,所以外科医生把原来的关节窝送给了她作为纪念。
不过,比起无意识的免疫系统来,我们的感觉器官更高级,例如触觉、味觉和嗅觉器官,它们是物理身体与综合意识之间的桥梁。不过现在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无论哪种生命系统,它越复杂高级,就越容易出现没料到的新弱点。
嘴里的警报接收器会在舌头被烫到之前告诉你扔掉手里的汤勺,但奇怪的是,辛香番茄酱里的辣椒含有一种叫辣椒素的化学物,它也会刺激到嘴里的接收器。薄荷糖让嘴巴感觉凉爽,是因为薄荷醇唤醒了寒冷接收器,它会让你像被北风吹过一样颤抖起来。对于嗅觉和味觉,元素也会耍一样的花招。如果有人把一点点碲弄到了身上,那他好几周都会散发出大蒜一样的恶臭,哪怕在他离开房间几小时后,人们也会知道他在这儿待过。糖比任何一种养分都重要,因为人类需要它快速提供的能量,既然人类在野外寻找食物已有上千年的历史,那你肯定觉得我们体内一定有非常精密的系统来探测糖。但铍——它是一种苍白色、不溶于水、熔点极高的小原子金属,看起来和环状的糖分子毫无相似之处——却能和糖唤醒一样的味蕾。
这样的伪装也许只是个玩笑,但微量的铍虽然是甜的,但随着剂量增大,它的毒性会急剧上升。据估测,全世界高达十分之一的人对铍过敏,这种疾病被称为急性铍中毒,完全就是周期表里的花生过敏。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恩里科·费米发现,就算是不过敏的人暴露在铍粉尘中,肺部也会受到损害,和吸入极细的硅颗粒一样会引发化学性肺炎。年轻的费米过多地吸入了这种化学“糖粉”,于是53岁时,他患上了肺炎,被牢牢拴在了氧气瓶上,他的肺已经被撕碎了。
负责咸味的味蕾也很容易被电流影响,但它只对特定元素的电荷感兴趣。钠激发出的咸味最强烈,但钠的化学表亲钾风风光光地骑在它头上,尝起来也是咸的。在自然界中,这两种元素都以带电离子的形式存在,舌头探测到的其实并不是这两种元素本身,而是它们所带的电荷。我们进化出分辨咸味的味蕾,是因为钾和钠能帮助神经细胞传递信号,也有助于肌肉收缩。如果没有它们提供的电荷,那我们的心脏就会停止跳动,大脑也会真正死亡。
当然,味觉如此复杂,咸味也没有上面说的那么简单,一些没有生理用途的离子也和钾、钠一样尝起来是咸的(例如锂和铵)。而钾和钠如果配对的元素不同,尝起来也可能是甜的或酸的。有时候,某种分子(例如氯化钾)在低浓度下是苦的,高浓度时却会变成咸的,就像电影里的旺卡一样变化多端。钾也能不表现出任何味道。匙羹藤的叶子里有一种名为匙羹藤钾的化合物,咀嚼生的匙羹藤钾能中和神秘果蛋白的改味性。葡萄糖、蔗糖和果糖能为舌头和心脏带来吸食可卡因似的快感,据报道,咀嚼匙羹藤钾会阻断这样的快感:即使在舌头上堆满糖,尝起来也不过像是一堆沙子。
这些事情告诉我们,追寻元素的时候,味觉实在是个十分差劲的向导。为什么普通的钾也能骗到我们,实在费解,不过对于大脑快感中枢来说,也许表现得过于热切、过于慷慨正是寻找养分的好办法。至于铍为什么能误导我们,也许是因为直到法国大革命以后,巴黎才有一位化学家提取出了纯净的单体铍,在此之前人类从未在自然环境中遇到过纯净的铍,所以我们还来不及进化出对它的本能厌恶。
生命体非常复杂,拥有蝴蝶效应式的混沌性,如果随便挑一种元素注入你的血液、肝脏或胰腺,那基本上只有天知道会发生什么。
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是20世纪另一位杰出的和平主义者,他曾将碘的例子当成灵魂不朽论的反证。“思考所用的能量似乎有其化学根源,”他写道,“比如说,缺碘会把一个聪明人变成傻子,智力现象似乎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换句话说,碘让罗素意识到,理智、情感和记忆都取决于大脑的物质状况。他没发现有什么方法能将“灵魂”从身体里分离出来,于是他推断,人类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人类所有光荣与大部分烦恼的源头,都完全来自化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