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阳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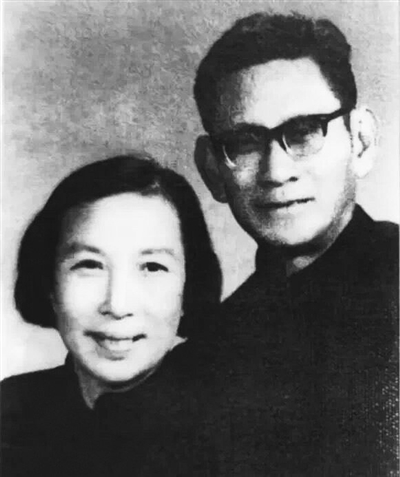
秦牧夫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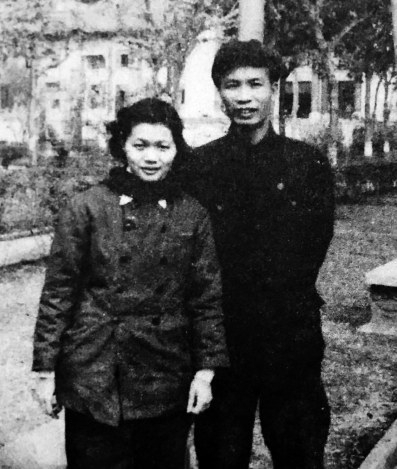
陈残云夫妇
上世纪80年代,我在花城出版社任职。为了保存名家资料,1986年秋,一位副社长带着时任总编室主任的我和摄影师,先后到广东著名老作家欧阳山、陈残云、秦牧家里访谈和拍照。流光浸润,回忆36年前家访三位文学大师的事,如清风拂面,至今难以忘怀。
欧阳山:笔底波澜情未老
我们先去位于广州梅花村欧阳山的家。因20世纪30年代陈济棠、孙科等官宦在此大建私宅且栽植了不少梅花,梅花村因而得名。欧阳老的家房子宽敞,我感觉客厅就像一个篮球场。墙上挂着一幅墨宝,现只记得其中几句:“浪涌云翻六十秋……笔底波澜情未老,胸中块垒志应酬……”
在放满书籍的书房,78岁的欧阳老此时安详地配合我们拍照。欧阳山人称顶着“四个光环”:一是18岁时他便发表第一部中篇小说《玫瑰残了》,19岁与鲁迅认识,28岁时在“两个口号论争”中坚定站在鲁迅一边,拥护“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1936年10月鲁迅病逝,欧阳山身穿长衫,手持“鲁迅先生殡仪”的大幅横额悲痛地走在队伍最前面,这是一种殊荣。二是1926年郭沫若介绍他进中山大学当旁听生。抗战开始后,在周恩来的教诲下在重庆入党。三是1941年到延安后参加毛泽东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写出了著名长篇小说《高干大》。1944年6月30日的《解放日报》发表了他写的速写《活在新社会里》,毛泽东看后大加赞赏并请他吃饭。所以欧阳山经常对人说:“鲁迅、毛泽东、周恩来、郭沫若是我的老师。”四是1959年创作的长篇巨著《一代风流》第一卷《三家巷》问世,因妙写岭南风韵,细说大革命时代恩恨情仇而轰动一时。
在与欧阳老谈到文学创作时,他说:“我在几十年文学创作过程中自撰了两句话:一是古今中外法,就是借鉴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表现手法。二是东西南北调,即是吸收中国各地方言土语的精华,尽量做到广收各家之长,博采各地之精。简言之兼容并包。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不容易。”
欧阳山是幸运的,终于在狂风暴雨后见到彩虹,这位“领一代风流的世纪大家”以92岁高龄于2000年9月26日魂归道山。
秦牧:为文的基调是爱
金秋的阳光温馨恬静,我们又去华侨新村的秦牧家。
对秦牧我心怀好感,源于一件切身的事。花城社是1981年建办,次年,我便调入去当编辑。记得校阅的第一本书稿就是散文泰斗秦牧的一本随笔集。我以虔诚之心逐字逐句拜读后,发现有几处用词不妥,要不要向这位名家反映呢?刚入行的我一时十分纠结。
我当时就听说在编辑中流传着某位权威作家的一句话:“我的书稿一个字也不能改!”这句话给我们带来心理压力,但内心又不认同。我斗胆写了一封信给秦牧,信发出后,心中一直忐忑不安,会不会触忤前辈?过了一个月,我突然收到他的回信,他称呼我“锡忠同志”,信中解释道:“我因赴京开会,延迟回来,今日才得读来信,时间足足相距一个月了。”他对我的指正不但不写一句辩解语,反而肯定地表示:“你的意见都很好。”言下之意同意作改动。最令我难忘的是他在信中写道:“我很高兴遇到你这样的编辑,能发现作者文字上纰漏粗疏之处的编辑才是好编辑。”40多年来,秦牧这句话如清风拂面,一直激励着我。
秦牧原名林觉夫,童年时在新加坡生活了10年,家境一般,生母和继母均是婢女出身。他经历了抗日和内战的灾难岁月。所以他为文的基调是爱,对人也谦和可亲。
这次我们来到他家拍照,他和夫人紫风十分热情。他住在普通民宅,布置朴实无华,只有书架上充盈氤氳书香。
秦牧曾几次来花城社开会,并对花城出版社有着深厚感情。我们也交谈过,有两件事令他十分感动:一是80年代初他心爱的散文集《花城》在京再版遇到困难。秦牧转而希望我们帮他出版。尽管当时花城社刚成立,人手经费都不足,但还是抓紧出版了《花城》,印数高达3万册。另一件事是,1984年2月出版了60万字的《秦牧自选集》,而且印数达1.5万册。家访时,我见该书放在书柜显眼处,他说:“这是我半生在文学园地耕耘所得的一个缩影。感谢花城社为我立了一个档。”
但天嫉英才,1992年10月14日凌晨,秦老起床赴书房时猝然昏厥倒地,遽然去世,年仅73岁。
陈残云:作家本色是战士
最后,我们去位于中山六路一条横巷内的时任广东省作协主席陈残云的家。这是一座老式楼房。早年参加革命,以小说《香飘四季》、电影《羊城暗哨》享誉一时的陈老时年72岁了,他面慈心善,有问必答,举手投足透着睿智的鸿儒之气。
从交谈中我进一步知道,陈残云不但是位大作家,更是一位坚定的革命者。他在桂林积极宣传抗日,险被特务用计抓捕。他还东奔西走营救同志,出任桂林文化界抗战工作队队长。他与田汉、黄药眠、周钢呜、华嘉、邵荃麟等文化名人一起工作过,投身抗日反蒋事业,后在罗浮山东纵司令部由李嘉人介绍入党。1953年他回广州搞专业创作,几年后电影剧作《羊城暗哨》一炮打响。
作家最关键的是视野。陈残云的作品非常生活化,和当年提倡深入生活分不开。他当过宝安县委副书记、广州市公安局办公室副主任等职。一起参加查案、办案,所以素材不少。开始时他很担心触动禁区,问广州市公安局的薛焰局长:“公安工作有哪些不能写的?”局长说:“你大胆地想吧,你想得出来的东西,我们公安工作都有,我们有的东西,你是想不出来的。”这番鼓励令陈残云放开了心中的桎梏,后来创作出更多意境奇谲的作品。
我们与陈老用广州话交谈,这使我联想到他被誉为运用粤方言创作的高手。他的小说中曼妙着粤语清韵,将“话头醒尾”、“一支针无两头利”、“隔夜仇”等粤方言用得恰如其分,让作品呈现一幅明丽多彩的南方水乡风俗画。2002年10月2日,88岁陈老驾鹤西去。 (摘自11月27日《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