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庭妇女们都踊跃学习

萨特和波伏瓦在天安门观礼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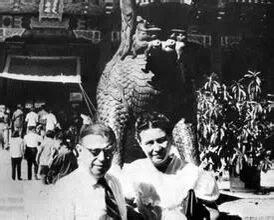
萨特和波伏瓦在颐和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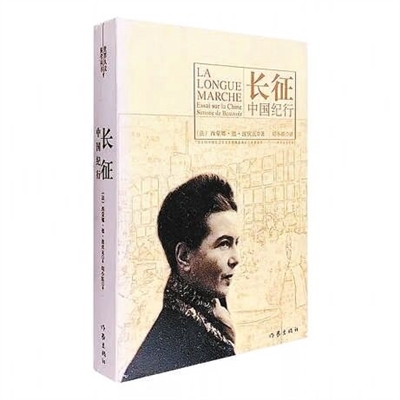
波伏瓦中国之行后的著作《长征中国纪行》
1955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向全世界发出“到中国来看一看”的邀请。这个邀请,吸引了大量西方共产主义者、左翼人士来到中国。其中,就包括两位存在主义大师——萨特和波伏瓦。在45天的中国之旅中,对于新生的红色中国,他们怎么看,怎么想,又擦出了怎样的火花呢?
一周的感受
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5年,外国文化界客人仅是20多个国家的550余人。万隆会议之后的5年,则激增到80多个国家的2万2千余人。
万隆会议一个月后,萨特讽刺麦卡锡主义的剧本《涅克拉索夫》首演,受到了共产主义者的热烈欢迎。他受邀参加在赫尔辛基举行的和平运动会议,波伏瓦也去了。在赫尔辛基,她和萨特都觉得,“社会主义也加入到我们的世界里了”。此时,中国政府发出正式邀请,希望他们在“十一”国庆之际,来中国进行为期两个月的访问。
从受邀之日起,波伏瓦就满怀激情地投入到中国之旅的准备工作中,她阅读了大量有关东方的资料。反共人士竭力贬低所有有利于新中国的见证,“为什么眼见之物就不能信、不能评?谁也不能长时间、大规模地蒙蔽整个国家”。
1955年9月,他们穿过西伯利亚,从莫斯科坐飞机来到中国。9月6日,他们终于落地北京。他们下榻的北京饭店,当初是法国人建的,如今住着各国代表,有1500人左右。外宾们的行程高度雷同,有时,对于官方早出晚归的安排,波伏瓦有些生气,特别是访问官厅水库的事儿:
从8点到12点,火车一直在隧道里穿行……为什么要让我们这样旅行?看看杂志上的照片和报道不就够了?
随着观察深入,波伏瓦自己领悟到了中方的执念:
在北京的各个城门,人们在徒手建造住房、学校、医院和办公楼。没有吊车,没有气锤,没有卡车——没有一台机器……他们就是用这种有4000年历史的技术来建造新北京的,建造大坝、铁路,汉口横跨长江的大桥也是如此。
作为新中国的见证者,萨特和波伏瓦受到了“程式化”的接待。即便提问题,得到的答案也很理想化。让波伏瓦苦恼的是,到北京一周,除了安排的参观,他们只能在北京饭店的阳台上“遥望”北京。
发现北京
正苦恼着,她有了新发现:作协送来许多英文资料,有书、有活页、有杂志,与提供给外国代表团的资料写法完全不一样。
在英文杂志中,他们读到了李富春“五年计划”的报告,“其真诚和严肃在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先例”。《中国文学》英文版是波伏瓦的另一个宝库。后来,她往往把参观的地方,看成小说更广泛、更具体的展现。“如果我没有见过中国的农村和农民,我就不可能那么深刻地理解丁玲和周立波关于‘土地改革’的小说。”
至于老舍笔下的龙须沟,她去现场看过了才明白:铺石路面,干净整洁的房子,没有垃圾和废物,这些法国的寻常事,在中国是一个巨大的胜利。
密集参观一周后,萨特、波伏瓦终于有了大把的自由时间,可以每天独自在北京的大街上散步。
“我在北京从来没有听见有人大喊大叫。当两辆自行车或人力车相撞时,骑车人会对视一笑。在我看来,这种好脾气是这座城市的魅力之一,这一点,我一到北京就发现了。”波伏瓦说。
一次,他们随便递出一张一元纸币作为车资,车夫摇摇头,表示太多了。他们又拿出一些小张纸币。车夫迟疑了一下,只拿了其中一部分。这种迟疑,让他们对北京人的诚实有了很深刻的印象。
在他们眼中,北京人“自然、放松、满脸微笑、多种多样,是智慧的”。就连千人一面的蓝咔叽布制服,也有了善意解读:在这个“大家一致”的国家里,人们感到比在贫富悬殊、穷人潦倒的国家里更舒服。
北京的魅力,在“十一”达到高潮。萨特、波伏瓦去东北参观了几天,再回来,北京的城市面貌就发生了巨大变化,街道焕然一新。“十一”当天,萨特、波伏瓦作为贵宾被送往观礼台。
在长达4个小时的活动中,穿着深蓝色棉布服的队伍川流不息,“第一个五年计划万岁!”“解放台湾!”“和平万岁!”50万北京市民高呼口号,喜气洋洋。
在中国待过很久的新西兰记者艾黎转过身问波伏瓦:“您能想象这不是发自内心的吗?”当然不,波伏瓦认为,他们的脸上没有奴性的表情,也不像是被迷惑的样子,他们对毛泽东的感情是发自内心的爱戴。
当天晚上,萨特、波伏瓦同100个代表团一道,被邀请到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焰火。因为是作家,他们与茅盾夫妇同桌。除去交谈,人们的注意力都在与大家问候的毛泽东、周恩来身上:
他们穿得跟大家一样,没有因为自己位高权重而板起脸孔,或要显示自己的身份,一点都没有……他们不但深具魅力,而且能唤起人们一种十分罕见的感情——尊重。
焰火后,萨特、波伏瓦走向广场,在欢歌笑语的青年中穿行,被他们的微笑感染,看他们跳舞,一直到凌晨。
10月3日,陈毅副总理接见了萨特和波伏瓦,老舍、茅盾、夏衍等也在座。“十一”的欢愉,让北京饭店宴会厅充满了对中国的赞许。但波伏瓦也怕中国被过度赞扬“捧杀”了,就委婉地以“老人”身份提醒刚到中国的“新人”:“在中国,有个错误一定要避免:那就是静止地判断问题。”
“看不到它所面临的困难就是无视它的努力。”她意味深长地说。
从北到南
在北京,萨特、波伏瓦感受着如日初升的活力,但作为新中国的观察者,仅看北京还远远不够。为此,他们不辞辛苦访问了东北的几个重工业城市,月底赶回北京参加国庆大典后,又南下南京、上海、杭州和广州。
工业化是萨特的兴趣所在。听说中国人决心用50年来追赶一千年的差距,他吃惊于这个任务的跨度。
但当他在同一天,既看了鞍山高炉,又看了附近土墙茅舍、徒手耕作的乡村,萨特感慨道:
每一天,每看一眼,必定要同时看到古老的中国和未来的中国,才能够懂得你们当前的情况,正是这个生动的矛盾所构成的。
扫盲运动也是萨特经常讲的一个例子。政府意识到他们不能提供足够的学校和教师,所以呼吁:所有识字的人要至少教他的一个邻居识字,这一运动开展起来,正是群众的自主决定,中国的面貌正以惊人的速度改变。他还比较了中国土改的成功与东欧国家集体农庄的失败,用苏联的失误来反衬新中国的英明和正确。
在广州,参观了大片拥挤和贫困的人家后,他们相信,中国政府没有向他们隐瞒中国,没有掩饰他们的广大农村,而是展示给他们看了。
从广东回到北京时,秋意正浓,大街上飘散着板栗的味道,树叶是塞尚画笔下的那种绿色。夜色中,萨特和波伏瓦在胡同中漫步:
重回北京,我才发现我是多么爱它,它没有上海那么嘈杂,也没有广州那么多彩,但在中国,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和美丽的灰色胡同相比……
作家们
当时,中国主要是把萨特、波伏瓦当成统战对象来接待的,对他们的理论与创作没有推介。在日内瓦大学任教的萨特研究专家德尼思·贝尔多莱先生讲过这么一个细节:萨特在北京与茅盾、丁玲等知名作家会面时,由于双方都没读过对方的作品,所以大家只好谈美食。
在中方作家回忆中,能想起来的对话,好像只有饭桌上的俏皮话。波伏瓦曾试图与中国作家探讨文学,甚至直接告诉茅盾本人,他的作品有矛盾之处,主角过于“高大全”了。但显然,对如何塑造人物,茅盾并不打算深谈。
新中国成立前就曾翻译萨特作品的罗大冈,终于在北京大学与大师见面了。“这位名重一时的西方大作家,给我的初步印象是出乎意料地谦和朴讷,平易近人。没有听到他在平常谈话时自以为是地高谈阔论,没有听他说过一句故作惊人之谈的俏皮话。”罗大冈在《悼萨特》中回忆。
让罗大冈印象最深的是,他早年翻译的《恭顺的妓女》,正准备在《译文》1955年第11期上发表。该刊编辑部主张将这个剧本的标题和结局,按照苏联的译本修改,以强化反美的意味。这样,不但结局相去甚远,连名字都换成了《丽瑟》。罗大冈当面问萨特是否同意这样改,萨特毫不犹豫地表示完全同意,豪爽的风度使罗大冈既惊讶又钦佩。
萨特视罗大冈为友,临别时特地问他需要什么法文书。罗大冈以为只是随便问问,所以也就不大在意地说,想要萨特的全部著作。后来,萨特果真从法国将他的著作悉数寄来。“像萨特那样认真,说话算数,把成套的书寄来,可以说是例外中之例外。”
相对于萨特,波伏瓦在中国更是知音难觅。幸而,陈毅把一个最合适的人派到了波伏瓦身边。
留法15年的陈学昭是法国文学博士,有着法式优雅。她也有很多层次很高的法国朋友,甚至还有一本法文版的《第二性》。陪同他们北上南下时,陈学昭和波伏瓦在卧铺车厢里,彻夜长谈,成了很好的朋友。波伏瓦形容,她非常聪明,极有教养,是个出色的观察者,她给我提供了各方面的非常宝贵的信息,嘴里没有一句废话和宣传。
鉴于萨特、波伏瓦的特殊关系,陈学昭还特地关照工作人员,给他们安排一套有两个房间的房子,两个房间要既独立又相通。这种细节,绝非一般女干部能够想到。
精神之旅
45天的访问后,萨特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对新中国的观感》,在《法兰西观察家》周刊发表了《我们所见到的中国》,盛赞中国的发展变化。
但在法国,反华势力依然强大,《世界报》《费加罗报》等几家主要报纸都大放厥词,讽刺萨特、波伏瓦是拿了中国的钱,替共产党唱赞歌。为了回应这些攻击,萨特接受记者采访,并组织了大量文章,发表在他任主编的《现代》杂志上。萨特还想写一本书,但未能如愿。
到1975年,萨特还在其《七十岁自画像》的长篇谈话中谈到中国。当记者问他:“在你的同时代人中,你有没有对别的人也予以完全的看重?”他的回答是:
毛(毛泽东)。我给与毛以完全的看重,至少一直到前几年。
我在余年还愿意去几个地方旅行,其中有中国。
萨特重游中国的愿望终未实现,但在他死后,却完成了在中国的精神之旅。1980年萨特逝世,《人民日报》称其为“中国人民的朋友”,在我国的知识青年群体中,掀起了一波“萨特热”。
波伏瓦看出1955年的中国不过是一种过渡状态,描述也是白费心机,“它需要的是解释”。于是,她用一年时间收集了大量资料,并结合自己观感,写出一部厚达500余页的著作《长征》。这部书几乎讨论了关于中国的一切,引用了无数资料和数据,还加上作者的实地考察和理性分析。
虽然颇费功夫,也清醒地知道这本书“明天就会过时”,但中国现在发生的故事太激动人心了,各个阶段都值得记录下来。
(摘自12月13日《北京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