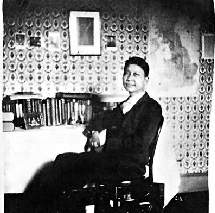
老舍在伦敦的寓所

曹靖华在苏联任教时翻译的《铁流》
老舍先生青年时代曾受聘于英国伦敦大学,在执教的五年中不仅教中文、编教材,甚至“跨界”到当时新兴的音像和广播技术中,录“声片”、做讲座。而现代以来,像他这样执教于域外学府的文化名家还不在少数。
“典型的老舍式的语言”
1924年秋开始,老舍在东方学院先后担任“中文讲师”“标准中国官话和中国古典文学讲师”,给中国语文系的学生教授汉语口语、翻译、古文和历史文选等,还和同事合教过道教佛教文选、写作课。据学者统计,当时系里的学生数量平均每年为五六十人。他的学生有统一编班的军官、银行练习生,也有基础各异、单班上课的老者、少年。而面对各种学习需求,比如“有的学言语,有的念书,有的要在伦敦大学得学位而来预备论文,有的念元曲,有的念《汉书》,有的要往中国去”,老舍作为系里唯一的中国教师,“是尽了自己的最大的努力的,开设了学生们所想学的所有课程”。他的责任感和专业态度赢得了院方的肯定。
老舍的中文教学情况除了写进散文《东方学院》,更多的成果已经凝结在他与英方教师合编的教材《言语声片》里。这套书分英文、中文两卷,可对照使用,另配16张唱片,录制了汉语语音基础示范和每课对应内容。老舍除了负责编写近半数专题的对话和课文,还以清亮的京音灌录了全部唱片,而且全书展示的汉字也是依照他的毛笔手书制版印行。
也正因为“典型的老舍式的语言”,《言语声片》渗透着浓郁的生活气息、人文情怀和文人意趣。老舍编写的部分有火车站、邮政局、洋服庄等场景,也有打电话、遇友、贺友人结婚等话题,现实感、代入感极强,又显示了中国特有的世态风貌。例如“我在正阳门大街买东西呢”,“请问到北京去的挂号信要多少钱?”再如《看小说》一课中,课文角色“甲”有如是表达:
说真的,近来出版的小说实在比从前好得多。因为新小说是用全力描写一段事,有情有景,又有主义。旧小说是又长又沉闷,一点活气没有。况且现在用白话写,写得生动有趣,你说是不是?
作为国际中文教育史上首部系统的有声教材,《言语声片》出版后,因其内容实用,体例科学,而被沿用了30年。
几乎是与编录教材同时,老舍还“触电”了新兴的广播技术,当过一次电台嘉宾。1926年,他受英国广播公司(BBC)远东部之邀,做了简短的中文知识广播讲座,内容涉及汉语声调、中文书写和文学引语。
1929年夏季,从伦敦大学离任后,老舍又在新加坡的华侨中学做过一学期的国文教员,“教的学生差不多都是十五六岁的小人儿们”。在《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中,他还拿这些华裔少年和伦敦大学的学生做了一番比较,而且“开始觉到新的思想是在东方,不是在西方”。
鲁迅亲笔书信成了教学素材
与老舍先生一样,将中国语言和文学传授给异国学子的还有著名翻译家、散文家曹靖华先生。
30岁时,曹靖华回到了他曾求学的苏联,从1928年起,受聘于列宁格勒大学,开始了五年的执教生涯。他所在的东方语言系开设有中国哲学、中国近现代史、中国造型艺术等课程,系里的领导者阿列克谢耶夫被视为苏联汉学创始人和领袖之一,其理想的课程体系是要多增加现代汉语和介绍现代中国的内容。但俄方教师有些还是沙俄时代被派到中国学汉语的,师从的是清朝翰林。所以,汉俄语言修养深厚又有翻译经验的曹靖华便成了教学新体系建设的“外援”。
实际上,曹靖华也的确让自己的工作在这所汉学重镇里绽放了异彩。他在一、二年级的教学大纲中规定,学生要朗读报纸和文章,着力练习发音和理解课文内容。二年级加入课文的复述和自由讨论,三、四年级在教材和词汇方面适当加深难度。各年级的学生都要持续练习楷书,还可选择行书。他们还阅读用不同字体写的汉语信札,鲁迅先生的亲笔书信也成了教学素材……
这样一来,曹靖华就改变了系里只教文言的局面,学生们整体接触了国内的五四新文学。这在当年的苏联不但开了风气之先,而且长远的效果是让列宁格勒大学走出了专门翻译、研究鲁迅等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的新一代汉学家。
在国际中文教育的历史道路上,我们还能看到,老舍身后是同一教职的继任者萧乾先生,与曹靖华执教时长相当的是在美国的梅光迪,冯友兰在华北协和语言学校也讲授过一年《庄子》,而海外华文教育领域,还留下了许地山、艾芜等人年轻时的身影…… (摘自2月10日《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