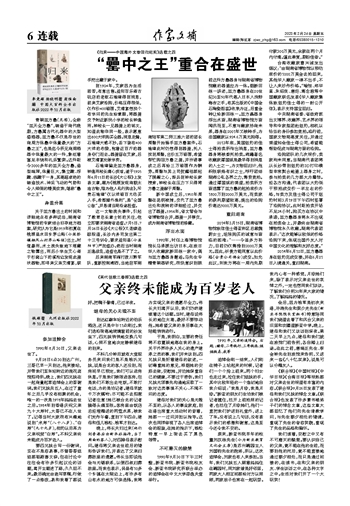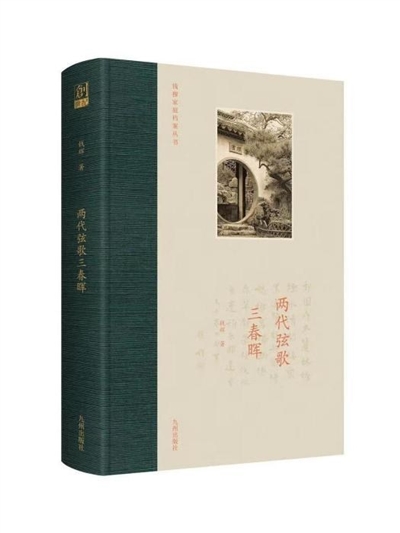
钱辉著 九州出版社2022年10月出版

1990年,父亲的追悼会。右起:继母、二哥钱行、三哥钱逊、姐姐钱易、我等
参加追悼会
1990年8月30日,父亲去世了。
9月28日6点30到达广州,三哥已早一天到达,他来接站,并带我们至车站附近的流花宾馆招待所。晚上,我们四兄妹在一起商量起草追悼会上的答谢词。我们兄妹共五人,在过了童年之后几乎没有相聚的机会,唯一的一次是1978年妈妈去世之后。1984年到香港庆祝父亲九十大寿时,大哥已不在人世了。记得当时大家很有兴趣地说到“米寿”(八十八岁)、“白寿”(九十九岁),相约以后再为父亲祝贺“白寿”。不料父亲终未能成为百岁老人。
要四兄妹合写一份谢词,实在不是容易事,尽管哥哥姐姐都聪颖善文辞,但在讨论中往往会有许多引起议论的话题,离开主题迷了路,久久回不来。最后确定由逊写草稿,行做了一点修改,易和我看了都说好。把稿子誊清,已过半夜。
继母的关心无微不至
到达红磡车站附近的伯乐酒店,还只是中午11点刚过。我们选沿街落地玻璃窗前的沙发坐下,四兄妹悄悄地交换几句话,心照不宣地决定静候继母的到来。
不料几分钟后就有大堂服务员来问我们是不是钱氏兄妹,说是台北的客人还没到,而房间早已预定,我们可以进房休息。于是我们被领进客房,但是我们不敢出去吃饭,不敢打电话,为的是怕记者。继母早就千万次嘱咐:尽可能不去招惹记者注意!她已被台北的记者搞得头痛至极。客房里由饭店总经理赠送的两篮水果,被我们充作午餐,直到下午四点,继母和侄儿钱松、钱军才到达。
晚上,伟长夫妇过来(他们到香港后由新华社接待,当了周南的客人),对四婶母表示慰问。继母将父亲去世前后的情形告诉我们,并表达了父亲归葬故里的遗愿。伟长当即说他会与无锡联系,以便四叔归葬故里。而我也表示,吴县有10多个乡镇在太湖边上,有许多有山有水的地方可供选择,我将为实现父亲的遗愿尽全力。伟长夫妇离开以后,我们仍然继续着这个话题。当时,继母说伟长的地位太高,最好不要惊动他。她希望父亲的身后事在大陆能悄悄进行。
于是,我明白,主要的责任将不容置疑地落在我的身上。关于外界许多人关心的遗产继承之类的事,我们并未谈到。四兄妹只是听着继母的叙述,一切尊重她的意见,根据她的安排去做,安慰她,并劝她保重自己的健康,不要过于悲伤。我们兄妹无须事先沟通地采取了一致对这类事漠不关心、不闻不问的态度。
继母对我们的关心是无微不至的,从各人的事业家庭,到在港出席重大活动时的穿着,她都一一过问并加以指导。这次也同样审视了各人出席追悼会的服装,在她的指示下,钱松特意一早上街去买了黑色领带。
不可磨灭的酸楚
1990年9月30日下午三时整,新亚书院、新亚书院校友会、新亚书院研究所联合举办的追悼会在中文大学邵逸夫堂举行。
追悼会刚一结束,人们刚在椅子上站起来的时候,记者们一个个抢上前来。两个妇女也走过来,拉住我们姐妹的手,其中比较年轻的一个急切地自我介绍说:“我是月珍,我是月珍。”新亚的朋友们生怕我们被记者缠住,拦开上前拍照的记者,也拦住了月珍她们,他们一直把我们护送到礼堂外,送上了车。没有说上几句话,没有表示我们的感激和谢意,这是至今还令我不安的。
原来,新亚书院早年的校董刘汉栋先生(今为新亚教育文化会主席)是苏州耦园主人刘国钧先生的胞弟,所以,这次追悼会,刘家也有人来参加。当年,我们兄妹五人跟着妈妈住在耦园时,同刘家曾是好邻居,两家大人相互间都给对方以照顾,两家孩子也常在一起玩耍。我内心有一种感觉,月珍她们来,除了表示对父亲去世的哀悼之外,一定也想同我们谈谈,了解我们分别30年来大家的情况,了解妈妈的情况。
会后,因为钱军是初次来港,许涛先生和梁少光先生(新亚书院院长室秘书)特意陪同我们绕道去看了和风台父亲的旧居和农圃道新亚中学。晚上,继母和我们又谈话到深夜。第二天早上九点,继母和我们就在旅馆门前告别,各自踏上归途。在此之前,唐端正先生、李金钟先生到旅馆来告别,又送来一些《八十忆双亲》,说是可以分赠友人。
《联合报》《中国时报》《中华日报》《台湾日报》等报纸都对父亲去世的报道有丰富的内容。《联合报》9月26日发表了继母和我们兄妹的悼念文章。《联合报》也发表了许多素书楼弟子们的悼念文章,这些文章大都回忆了他们向先生请教学问,与先生朝夕相处的情境, 重现了先生的音容笑貌,重现了先生的品格和胸怀。
我们读着,安慰之中又有不可磨灭的酸楚。要认识自己的父亲,竟不能在他的生前,而要到他的死后,竟不能直接地通过朝夕相处,而只是通过间接的,在读书,在和父亲的朋友、学生谈话之中,在各种文字之中。生活对我们开了一个大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