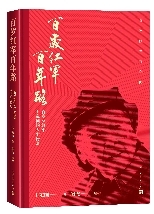
王定国著 谢飞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2月出版

1964年妇女节,王定国与母亲(前排中)、长征中的女战友合影
第一次上学
我第一次走进学校的大门,不是在少年,而已经是十八九岁的青年人了。
苏维埃学校是根据川陕省第二次党代会上的决定成立的,在通江和巴中各成立一所苏维埃学校,专门培养地方工作干部。苏维埃学校校长姓周,副校长就是张静波,当时川陕省委的许多干部都轮流来校讲过课。
我参加的是苏维埃学校第二期培训。这期的学员有400多人,女生占了一半多。
土地法、劳动法是由张静波讲课。他对人很热情,工作认真,每次上课后都要问我们听懂没有,记得住记不住。张静波在营山搞兵运和教育工作时住在我家,因为是熟人,我见他不紧张,上他的课,我也觉得容易些,自然也就学得好一些。别的教员多是鄂豫皖来的,说话带有方言,我因语言不通,听课很困难。我们又大多不识字,学习全靠用脑子硬记。
我们从营山到巴中之前,营山县苏维埃政府特意从浮财中,挑了一些颜色好的缎子和衣服给我们每人一件,我改了改,穿上很合身也很漂亮。张静波让我换掉,我不服气。可张静波坚持要我换上他从保卫局处决的犯人身上脱下来的一件粗蓝布褂子。我心里非常别扭,但是看到张静波那样严肃,也不敢坚持了。后来我才知道是什么原因。
有一次,我和龚玉珍聊天,说到我们家乡打土豪没收地主老财的洋钱都用箩筐装,不知怎么,这话让人传成了我家里的洋钱多得用筐装,这样一来,我竟被怀疑为地主小姐了。当时由于张国焘的极“左”政策,成分不好是要受审查甚至被杀头的。要不是张静波和政治部主任一再替我解释,我可能早就没有今天了。
我顺利地通过了各门课程的考试。我站在桌子上,面对全体学员和教员宣讲土地法,这是我下功夫最深的一门课,结果在全体学员的考试成绩中,我获得第二名。
张琴秋大姐
毕业前,我们参加了土地复查工作,也算是实习。就在这时我结识了张琴秋大姐,她被派到红江县任县委书记。
张琴秋大姐平日穿件双排扣子的列宁装,剪短头发,戴着军帽,绑腿也打成人字形,很利索,苗条的身材扎了条宽皮带,腰间挎了一支小手枪,人又长得漂亮,真是飒爽英姿。
我自从1933年跟上队伍出来,也接触了许多女同志,大部分和我一样是不识字、受过很大苦的农家女。像张琴秋这样文武双全的妇女干部这还是第一次遇到。以前听刘瑞龙上课时说,在川陕苏区一带,张琴秋是唯一念过好几门外语的大学生,又是1924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她性格爽朗,没有架子,我非常佩服敬重她,我们一同去的二十几个女孩子,也都很喜欢她,很快就和她混熟了。我们只要有了困难就找她。大姐只要有空儿,就一定会给我们安慰鼓励并教给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
有一天夜里,土匪包围了县政府,张琴秋亲自跑来叫我们,带着我们冲出去。在这次战斗中,我亲眼看见张琴秋是那么勇敢机警,指挥战斗又那么沉着果断,在她的指挥下,土匪很快被打跑了。
在红军新剧团里
1935年2月,中央红军北上,长征到达贵州省。为迎接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的会合,川陕省委和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决定扩大宣传队伍,将原有的剧团规模扩大。我因为平时爱唱爱跳,组织上就将我调到剧团工作。
这个剧团先后直属于川陕省委和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是红军时期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一个文艺团体。它的前身最早是陈其通领导的一个小宣传队,后来逐步扩大,随着川陕苏维埃的建立,由一个剧团发展成四个剧团。这个剧团的名称先为“兰衫剧团”“工农剧社”,群众都称之为“新剧团”。
我被分配到新组建的四团,我在剧团参加唱歌、跳舞,也演新剧,扮演劳动妇女之类的角色,而我的主要工作是负责服装、化妆、演出部门的事情。
为谢老缝毛衣
1935年6月中旬,红一、四两个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在夹金山麓胜利会师。在大会师的大好形势下,中央领导日夜开会,准备共同北上。我们剧团经过两河口、毛儿盖来到卓克基,大家都为过雪山做准备。
有一天,我正和几个剧团同志在山坡下聊天,见一位一方面军的老同志手拿衣物从山坡上走下来,他面带笑容走到我面前说:“小同志,请你帮帮忙,要过雪山了,请帮我把这两件单衣合起来装上羊毛,缝成一件羊毛衣。”我当即接过来说:“行,我今天就缝好,明天我就给你送去。”这位老同志连忙道谢说:“那就谢谢你了,我叫谢觉哉,就住在这山坡上,是一方面军干部休养连的。”
第二天我将缝好的羊毛衣送去,谢觉哉见了远远地招呼我,说:“谢谢你,缝得很好。”并将身旁的董老(必武)、徐老(特立)给我做了介绍。我自我介绍是四方面军剧团的,叫王定国。在我向他们告别时,谢老特地嘱咐我:“小王同志,你们过雪山的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回去告诉同志们多准备一点辣椒,可以御寒。”谁曾料到,这次与谢老的偶然相遇,竟使我们后来成了终身伴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