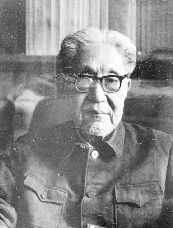
初识志摩
孙大雨(见图,1905-1997)祖籍浙江诸暨,出生于上海,父亲孙廷翰是清朝翰林。1922年初秋考入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高等科后,孙大雨参加了“清华文学社”,后编辑《清华周刊·文艺增刊》。这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校园文学社团。
1924年春,蔡元培、梁启超邀请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华。泰翁4月12日到上海,徐志摩、郑振铎等到汇山码头迎接。23日到达北京,5月1日晚,开始在清华大礼堂作系列演讲,这是此次请他来中国的主要议程。正在清华高等科读书的孙大雨获悉泰氏入住清华园,即刻怀着崇敬的心情前去荷花池畔后工字厅泰翁下榻处请求见面。果真受到泰戈尔的热情接待,他们谈兴甚浓。也许,在这次与泰翁难忘的见面中,孙大雨也第一次见到了徐志摩。
交谊日深
1925年5月,闻一多留学回国,搬进京城新寓后,居处较宽敞。正如徐志摩在《诗刊弁言》中所说:“我在早三两天前才知道闻一多的家是一群新诗人的乐窝,他们常常会面,彼此互相批评作品,讨论学理。上星期六我也去了。”这个“新诗人的乐窝”,是徐志摩与孙大雨、朱湘等诗友经常聚会的地方。1926年4 月1日,《晨报副刊·诗镌》创刊,每周一期,徐志摩邀请他们轮留做编辑。自此,孙大雨与徐志摩有了更多交往,遂成莫逆之交。
1925年7月,孙大雨从清华毕业,他第一站去了长沙,凭吊屈原,以缅怀我国诗歌先祖。第二站去了浙江普陀洛珈山圆通寺,借住在寺庙里,面壁两个多月,伴一盏青灯,冥思苦想,探求新诗的出路,并创建出“音组”理论。以后,他写出数万字论文《论音组》和《诗歌的格律》。他说:“我向往诗歌里情致的深邃与浩荡,同格律声腔相济相成的幽微与奇横。”由此,孙大雨第一次以音组结构创作了十四行体新格律诗《爱》,1926年4月10日,徐志摩将此诗刊发在《晨报副刊·诗镌》第二号上,这是徐第一次刊发孙大雨的诗作。
孙大雨回国后,得徐志摩介绍,赴武汉大学任外文系教授,月薪两百大洋,生活待遇相当不错。1931年4月和10月,《诗刊》在第二和第三期上,刊出孙大雨长诗《自己的写照》前300行,徐志摩在第二期的《前言》中写道:“这300多行诗我个人认为十年来(这就是说自有新诗以来)最精心结构的诗作……”徐志摩对孙大雨的如此诗歌评说,还没有出现在第二个新月诗人身上。
1931年4月,在徐志摩主编的《诗刊》第二期上,发表了孙大雨翻译的莎士比亚诗剧《黎琊王》。1931年10月《诗刊》第三期上,徐志摩又刊发孙大雨的《罕秣莱德》。虽然是节选试译,徐志摩仍给予很高评价。这是徐志摩生前最后一次刊发孙大雨的译著,成为绝响。
永志怀想
1926年10月,徐志摩与陆小曼婚后回到上海定居,孙大雨和妻子孙月波与之常相往来。1931年7月16日,徐志摩在给北京胡适信中写道:“说些开胃话吧!昨晚我家大集合,有洵美、小蝶夫妇、朱维基、芳信、孙大雨、高植。”徐志摩1931年8月在上海出版《猛虎集》,将新著题赠给孙大雨,上款称“大雨元帅正之”,而落款则自谦“小先锋志摩”。由此可见,比徐志摩小9岁的孙大雨,在其心中占有何等分量。此书出版仅三个月,徐志摩因飞机失事辞世,成为留给孙大雨的最后礼物。
孙大雨在1926年赴美留学之前,和1930年归国之后,其间约三年时间,是他与徐志摩交往最多、过从甚密的时刻。就在徐志摩辞世前两个多月的9月14日,徐志摩为孙大雨去北师大任教一事,致胡适的信中说:“还有孙大雨的事,也使我觉得为难,他非得有一个月的薪水到才能走路。无论如何得寄他至少300元,否则连累他半年失业,我如何过意得去。”之后10月29日,徐志摩在给陆小曼的信中,又一次提到孙大雨:“大雨家贝当路那块地立即要出卖,他要我们给他想法,他想要五万两,事成我要二厘五的一半,卖否由大雨决定。”孙大雨卖宅地救急,徐志摩乐做中介,可见当年新月诗人间的相互信任。
谈起徐志摩,孙大雨多次对家人和朋友说:“徐志摩为人极好,单纯到近乎天真。”在与别人的通信中,他也会称赞徐志摩:“天真纯朴,很可爱,是我的好朋友。我和他接触中,时常听到他谈起史沫特莱。”念兹在兹,孙大雨不忘徐志摩对他的扶持之恩、诗友之情。
特别要提到的是,徐志摩生前曾对孙大雨有过重托,把他一个棕黄色小皮箱寄存在孙大雨处,里面装有徐志摩的手稿、书信、日记等重要私人资料。可见徐志摩对孙大雨的信任。徐去世后,孙大雨把箱子小心翼翼地藏在老屋最隐秘处。可是,在十年动乱的抄家中,这个小皮箱被抄去后至今不明下落。孙大雨曾留有抄家物资归还清单手迹,其中有未还的“徐志摩手稿一箱”。孙大雨生前说起此事,痛心至极,深感对不起故友。 (摘自4月12日《中华读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