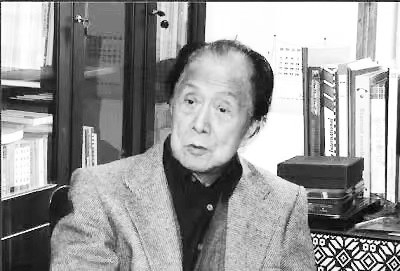
在诗与书的陪伴中, 彭燕郊(见图)度过了多磨多难而又自甘寂寞的一生。
用衣服换钱去买书
彭燕郊讲自己找不到书的状态,“要是找不到,就会整天觉得茫茫然,坐立不安”。如果有幸寻到,便如获至宝。作为资深淘书人,彭燕郊也遇到过好多种情况:
曾经见到,当时以一念之差没有买下来,一直为之追悔莫及,这回可又遇到了,再不能失之交臂;听人说起过,或读过介绍文章,可惜缘悭一面,忽然淘到,喜出望外;本来有这部书,种种原因,得而复失,耿耿于怀不知多久,久别重逢;从未见过不知世间竟有这样的好书,无意中发现,喜出望外;等等。
彭燕郊一生秉持节约,买书却很慷慨。1942年,彭燕郊在桂林时,“在旧书店见到李伟森译的《朵思退夫斯基》,是他的夫人写的回忆录,翻开书读两页就被那如火如荼的激情吸引,立刻有这本书可能影响我一生的感觉,一定要买下来,没办法,只好把用友人罗岡送给我的用萍乡夏布做的一套唐装卖掉换到这本书。当然,后来也没能保存,到处找,也再没见到这本书,再也忘不了”。
1944年,桂林处于大疏散中,时局日益动荡。为了生存,彭燕郊不得不到柳州去卖衣物换钱,然而,路遇匪徒抢劫,书却成了唯一的留存物,实乃不幸中的万幸。
走过了那段艰苦的岁月,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直到1950年,彭燕郊一直在北京的报社工作,业余时间便去各大书店或书摊淘书、淘唱片,自称已成为“大玩家”,他深觉再沉溺于北京的繁华之中,只怕是会迷朱自己,因此应湖南大学谭丕模之邀,南下长沙当起了大学教授。虽然长沙不如北京书店多、好书多,但是对彭燕郊的吸引力只增不减,旧书店基本上都有彭燕郊的踪迹。
没条件创造条件
彭燕郊对书的痴爱不因任何阻碍而减少,没有条件便自己创造条件。20世纪50年代中期,彭燕郊因“胡风案”被关押近一年,因为自己无法到书店购书,便托人到新华书店购买。1950年代末,彭燕郊到街道工厂做供销员,成天在外繁忙地跑业务,却正好让他有很多机会去转旧书店,“成天在全市各处跑,积习难返,上街总要到古旧书店转一转,虽然经济困难,但书癖难戒,有些书节衣缩食也一定要买”。
到了“文革”时期,彭燕郊的家被抄了六次,多年的藏书也都被没收,视书籍如生命的彭燕郊度过了一段难熬的岁月。在被关押的那段时间,他无法像之前那样托人购书,只能在狱中写诗,写在小纸条上,或记在心里,待出来后再眷写。
1979年3月,湘潭大学聘请彭燕郊到中文系任教,同年10月,他得到平反。相较于之前在工厂的日子,这一时期的彭燕郊工资待遇提高了,他淘起书来更加“疯狂”,或许是为了弥补早年错过那些书的遗憾。
彭燕郊退休后,爱书之心仍不退休,退休金除了买药治病,差不多都拿去淘书了。彭国梁是长沙有名的书虫,他这样形容彭燕郊淘书的情景:
他经常是一包一包、一捆一捆地买,提不动,就打的。
书是彭燕郊的命。他每次借书给他人,先用牛皮纸将书包好。无论是自己的还是他人的书,他都非常珍惜。书友王平曾不小心弄丢他一本书,“他很生气,眼泪都出来了”。有一次,彭燕郊把朋友的书转借给他人,书还回时几乎散了架一样,彭燕郊很是难过。
赠书往来佳话
彭燕郊爱读书,也常和友人互相借书。无论是读书人还是工人,无论是同辈还是小辈,只要爱读书,彭燕郊都会视其为书友,互相分享读书的乐趣。
彭燕郊和汪华藻曾是师生。他们退休后,因都住在长沙,彼此间也有往来。彭燕郊知道汪在收藏《红楼梦》,只要遇到不同版本便会收集送给他。若是汪华藻不在家,他便把书从门缝塞进去便走。
张铁夫(1938-2012),湘潭大学教授,普希金研究专家。他在《我所认识的彭燕郊先生》中回忆,自己写“普希金研究三部曲”时,彭燕郊“把珍藏了六十年的《译文》新二卷第六期(《普式庚逝世百年纪念号》)和珍藏了五十七年的《普式庚论》一书送给了我”。古有宝剑赠英雄,今有珍本赠学者。
施蛰存晚年开始处理自己的藏书,也不再接受朋友的赠书。1994年1月17日,他给彭燕郊去信:
兄以后不要再送我书了,我也无力看书,子孙一代,没有一个是搞文学的。我的书在渐渐处分,不必再增加了。
不过,同年5月19日,施蛰存给彭燕郊复信:
昨晚翻阅兄所编《现代散文诗名著译丛》见广告中有《夜之卡斯帕》及《地狱一季》二书,不知印出了没有?如已印出,可否还能代我各买一本?
彭燕郊曾在书店遇到一位爱读书的青年技术员,得知他有一本《飘》,想借来看看,但是技术员不肯。最后彭燕郊用《安娜·卡列尼娜》换到了《飘》,虽有得有失,但彭燕郊坦言:
能够解馋,就已经叫人十分满足了。
1970年代前期,彭燕郊在长沙北区阀门厂做油漆工。他经人介绍认识了在南门口的街道工厂做车工的王平。两人住一南一北。据王平回忆,彭燕郊每周六下午下班后都会在南门口公交站下车,步行到他家送书,送完书后,拿上王平看完的书就走。王平笑称“就像地下党情报员接头似的”。(摘自《书屋》2024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