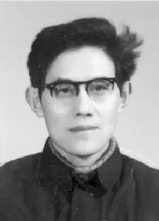
少年意气袁良骏
袁良骏先生(见图,中年时期)原是我们北大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老师,后去社科院文学所鲁迅研究室。他80岁患肺癌去世,不做任何仪式,以不打搅社会为原则。他生前积极作为、建功立德,死后放下一切,超脱平静。即使圣人处分生死,其完善度也不过如此吧!
袁老师很用功,涉猎广,敏锐,论著源源不断地面世。他说王瑶先生说他的文章“汪洋恣肆,如河水泛滥”,后来才醒悟这是在批评他。他确实是思想奔放至奔溢,才华横溢至横流,思想文字表达敢舍敢取,放而不收,似乎也有测试学术表达的底线之意。他为人爽朗率真,我有时觉得他的行为像是儿童在装大人,有少年意气。
林默涵当中国鲁迅学会会长时,袁老师出任学会秘书长和学会法人,把学会活动主持得热热闹闹、风生水起。他主持学术会议的风格是热烈开朗,插科打诨,知无不言。会议开始时一本正经,西装革履的,可是说着说着便眉飞色舞,进入自由状态。
1999年,鲁迅学会在北京邮电宾馆开年会,袁老师发言批评当代文坛“三弊”,批评影视界戏说历史成风,消解崇高什么的,都一本正经,但到了批评第三弊“文学作品中性描写泛滥”就憋不住了,他从棉棉和卫慧的小说中摘取一些不便启齿的段落大声读出来,读了一段又一段,最后被张恩和老师呵斥一声“够了!够了!”才大笑着停止。
性情中人杨义
和袁老师接触稍多是1991年参加曲阜师大的“鲁迅与孔子”学术研讨会。那时中国的交通还不如今天这样便捷,能买到火车卧铺票也算个“小确幸”。记得我是排队一起买了杨义、孙郁的三张硬卧票,似乎还是从永定门车站上的车。
那次会议是令我印象深刻的一次旅行。一是因为第一次见到杨义。杨义在80年代,虽然是和钱理群、赵园、王富仁、刘纳、吴福辉、蓝棣之、凌宇齐名的青年学人,但他却从不参加任何学术会议,声称板凳甘坐十年冷,不在学术上做出成绩来绝不参加任何学术会议。邢少涛和冯奇都告诉过我文学所的一个传说:杨义在家写作,因为孩子哭闹,就让妻子住回娘家。家里停电,就把手电筒吊起做灯,继续写作。1991年,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已经正式出版,得到学界的高度评价,可能杨义觉得学术上已有小成,因此有资格出门参会了。
我那时是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文学室编辑,因一起购票之故,约定杨义、孙郁一起赴会曲阜。在永定门车站等杨义时,看到远处一个人大包小包、很狼狈地从人群中挤出,满头大汗地过来,才知道他就是江湖盛传的奇人本尊。原以为他不轻易与会,没想到却是老农民式的踏地、实在,他的不出席学术会议完全不存在任何高妙、料峭的理由。我心中学术界的神异传说就这样幻灭了,不免失望。但杨义的真实存在,他的专注、自负,以及一种奇特的无视客观环境的主观性,令我惊异。那种无视旁人,不顾及他人的唯我主义,若发生在别人身上,恐怕令人讨厌。但在杨义那里却出自性情,并且天真烂漫,像孩童那样自然地做了宇宙中心。
在泰山游玩的时候,杨义是走三五步就要和泰山合个影,一路上我几乎成为他的专职摄影。孙郁是路上见老人就要过去搀扶,令我反省为什么我从未具有这种主动积极的善意——毕竟我也自诩善良,却发现自己的善良是消极性的,而孙郁的善良是积极、主动的。
爽朗的笑声
这次会议令我印象深刻的第二个原因,是发生了林非先生的会议闭幕致辞被打断事件。他闭幕致辞说,在会上听到一些意见,有的比较正确,有的较有争议……但这时他的发言却突然被两位与会学者起立打断了。其中一位比较年轻,会上发表观点,贬低鲁迅的小说成就;另一位某大学领受国务院津贴的古代小说研究者则有点年纪了,他贬低鲁迅的传统文化修养,说鲁迅读书不多,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所知有限云云。这两位神情激动地质问:到底哪篇论文的观点不正确?请林会长指名道姓地指出来!林非先生的应对当然非常机智和得体,他说请二位少安毋躁,每个人的观点都不可能绝对正确,都可能存在错误。请让我先说完话再发言好不好?
致辞完毕,主持会议的袁良骏老师走上台马上宣布:“散会!”这激出火花的一幕,会后大家自然是议论纷纷。
此事不久,袁老师在《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杂文,文中举例某学术会议上某些学者“妄议”鲁迅传统文化修养浅薄,也没有指名道姓。
一天我在《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正常上班,收到有人寄来的谴责和控诉信,指责袁良骏捏造、歪曲和打压他在“鲁迅与孔子”学术讨论会上的观点,说他从来都认为鲁迅的传统文化修养极其深厚,从来是崇敬鲁迅,且有所附论文为证。我翻阅所附文章,发现提交会议的那篇论文已在刊物正式发表,只不过作者把批评鲁迅的观点全部180度大转弯,改为对鲁迅的肯定和赞扬!我便给作者回了一封信,大意是:那天会议我也在场。大家都长有眼睛和耳朵,你接受批评改变论文观点是好事。不要再闹了,否则就是欺负学界无人。
几年后我和袁老师论及此事,他昂头发出一连串爽朗的笑声,丝毫没觉得我的回复有什么不妥。 (摘自《随笔》2024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