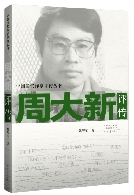
(摘自《周大新评传》,河南文艺出版社2025年1月出版)
1972年6月,周大新被提拔为连部的文书。文书可以进入连部的仓库,他意外发现这里有几本盖有“内部书,供参考”红印章的书,其中一本是苏联小说《你到底要什么》。翻开才发现,书中夹着纸条,上面写着:“本书是供干部们了解修正主义在苏联作恶的情况而印的,要求干部们一定要带着批判的眼光去看,要看出问题来。”周大新不是干部,看此书有点越级犯纪律,但当时可看的书太少,他抵抗不住诱惑:
当天晚上全连熄灯之后,我偷偷把书由仓库拿出来,然后钻进被窝,打开手电看了起来。
他读得如痴如醉,这部小说写的是城市年轻人的生活,其中有关于爱情,关于追求自由生活的描述。这些内容读来十分新鲜有趣。周大新用了三个晚上把书读完,想着自己要是能写出这样的小说就好了。
这本书让周大新知道,原来除了新华书店卖书,还有另外卖“内部书”的地方。之后,他开始打听卖“内部书”的地方,终于找到团部所驻县城的新华书店,向销售科长表达了想买“内部书”的心愿。科长见周大新是军人,很客气,在办公室接待了他,但还是为难地表示,买“内部书”需要团政治处开证明。周大新说了很多好话,对方感受到他是真心要买书,就叮嘱“只供你自己读,不能外传”,便允许购买。周大新喜冲冲地跟着他进入“内部书店”——一间很小的房子,里面放着几排摆满书的书架。大多数是一些外国领导人写的关于政治方面的书,还有中国人描述外国情况的书,苏联的小说只有一本。但机会难得,周大新还是把书装满了军挎包带回连队,开始悄悄地阅读。
此后,周大新开始频繁地与“内部书店”打交道。调到泰安师部后,当时他已是干部,买“内部书”终于名正言顺。1978年他调到济南军区机关时,又和省新华书店卖“内部书”的老耿建立联系。那时虽然不再明确印上“内部书”的字样,但发行范围还是有明确限制。老耿不限制周大新买书,那些年他读了很多在新华书店公开柜台上买不到的书。其间,买了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等书来读,觉得这位作家很伟大。他强调博爱,爱这个世界、爱所有的人,该观点一直深植在周大新心底,他觉得人生活在世上不容易,爱是最重要的。
孙绳武曾撰文回忆“内部书”确定、出版的过程。20世纪60年代初,当时作家协会的领导曾召开了两三次外国文学情况交流会,会议由当时作协负责外事工作的严文井主持,参加会议的有罗大冈、杨宪益、曹靖华等老先生,以及《世界文学》编辑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少数同志。会议初期的中心议题是西方文学的新现象,因为20世纪四五十年代文学界对苏联、东欧了解较多,同西方接触极少。这几次会上谈到了英、法、美的一些作品及倾向,例如,反映这些国家中青年(尤其是工人)对社会颇为不满的情绪,即所谓“愤怒的一代”的代表性作品,并决定选几种译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出版。其中有《往上爬》《愤怒的回顾》《在路上》,后来还加上了《星期六晚上和星期日早晨》。这些就是不公开发行、不做宣传的所谓“内部书”出版的开始。过了不久,“内部书”“开始以翻译反映苏联文学中的一些新的倾向的作品为目标。最先的一本是美国人编选的暴露苏联生活中阴暗面的《苦果》”。
这一时期,周大新开始系统读书,虽然年轻,却很想在测量方面写本书,就买了一些测量方面的书籍。同时开始读《论语》《聊斋志异》《老残游记》等书,也尝试写作一些诗歌,当时文书的一个任务就是出黑板报,在空白处需要诗歌来填满,周大新就自己编一些诗句填在上面。
1974年,时值“批林批孔”,军部领导要来部队听讲解柳宗元的《封建论》。领导先是安排一位班长讲,但效果不好,临时安排周大新讲解。周大新接到任务后只有一个晚上的准备时间,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讲课,就回忆自己的老师当年如何讲。第二天的讲解,因详略得当、板书美观,他得到首长的认可,被提拔做排长。
这一次的提拔改变了周大新的人生命运,使他摆脱了复员回家种地的担忧,并住进团部大院。周大新第一次住进楼房,感觉很新鲜。团队大院里有一个灯光球场,有球赛的日子非常热闹,球场四周被官兵们挤得水泄不通。最威风的时候是会操,全体官兵军容严整,在高亢的口令声中做着操练动作,队伍在行进时雄壮的步伐有排山倒海之势,呼出的口号能惊飞几里地远的鸟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