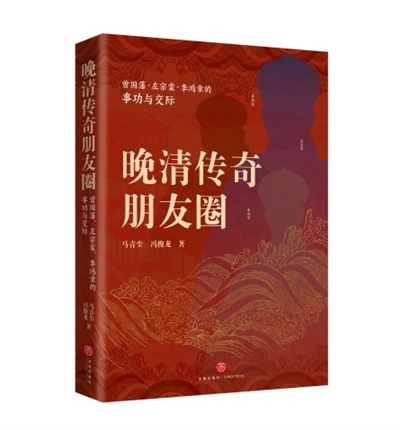
马青尘 冯俊龙著 天地出版社2025年5月出版

“此血所以报国也”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为收拾甲午战争残局,李鸿章赴日本马关谈判签约(见图,签署《马关条约》时的李鸿章)。3月24日下午4时,进展十分艰难的中日谈判结束第三次会谈,满怀心事的李鸿章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出春帆楼,乘轿返回驿馆。就在李鸿章的轿子快要到达驿馆时,大街上的人群中突然蹿出一名日本男子,奔至轿前,趁左右未及反应之际,向李鸿章面门开了一枪。李鸿章左颊中弹,血染官服,当场昏厥过去。
一时间,现场大乱,行人四处逃窜。行刺者趁乱溜之大吉,躲入路旁的一个店铺里,后来很快被抓捕归案。警方查知此人名叫小山丰太郎,是日本右翼团体“神刀馆”的成员。他不希望中日停战,更不愿意看到中日议和,一心希望战争进行下去,所以公然刺杀李鸿章,企图进一步激化中日矛盾。
李鸿章已年近七旬,中弹后血流不止,子弹卡在他左眼下的骨头缝里,没有医生敢动手术,李鸿章给朝廷的电报只有六个字: “伤处疼, 弹难出。”医生们经过会诊, 一致认为应该立即手术,取出子弹,并静养多日,不能再稍劳心力。李鸿章闻言从床上挣扎坐起,慨然道:“国步艰难,和局之成,刻不容缓,予焉能延宕以误国乎?死生有命,我宁死无割!”第二天,见血满袍服,他叮嘱将这件衣服好好收藏起来,怆然长叹道:“此血所以报国也。”
“只知李中堂,不知中华耳”
岂知,李鸿章非但没有如愿“报国”,而且身背“卖国贼”骂名。李鸿章签订的《马关条约》,是他一生代表清廷签订的三十多个不平等条约中的一个。但是,李鸿章只是清廷委任的“钦命头等全权外交大臣”,是慈禧绥靖外交政策的忠实执行者,代人受过而已。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这是李鸿章对自己的总结。晚清最后的苟延残喘,都是在内忧外患中的无力挣扎。李鸿章再为清廷“勉力涂饰”,也不可能挽救将倾大厦于既倒。孙中山先生的回忆,或许最能说明问题。他说庚子事变之前,家乡人知道他在搞革命,但是都把他当成乱臣贼子,希望他革命失败。1900年10月,趁着庚子事变,孙中山先生在惠州起事,这一次革命虽然也失败了,可是人人觉得惋惜。这个例子适合作为李鸿章一生努力挣扎的注脚。
李鸿章曾经颇为自得地说:我办外洋交涉数十年,不敢谓外人如何仰望;但各国朝野,也总算知道中国有我这样一人,他们或喜欢与我见面谈谈,也是普通所有之事。李鸿章以“懂外交”著称,其外交声望,在当时的中枢大臣中无出其右。当时,外界有这样的说法:“只知李中堂,不知中华耳。”
李鸿章在去日本之前,与众臣议论媾和,坚决反对割地,声称:“割地则不行,议不成则归耳!”幻想破灭后,上奏光绪,要求“面谕训诲”,得到光绪帝谕令“以商让土地之权” 后,再往赴日本;在日本遇刺之后,头缠绷带,强忍剧痛,抱着“争一分是一分”的态度,在谈判桌上拼尽全力,苦苦挣扎,“几至于乞怜,舌敝唇焦,磨到尽头处”。李鸿章的据理力争,最终使清廷赔款减少三分之一,割地减少近二分之一,使日方在最初提出的和约底稿上作出了较大让步。人们只看到李中堂的风光无两,却很少有人知道他内心的油煎苦熬。
“尽一分心酬圣主,收方寸效作贤臣”
不过,挣扎在腐朽泥潭中的晚清, 以慈禧为代表的统治者,不可能让崛起的汉人重臣操持航向,李鸿章等时代精英倡导的“变法”,只能浮于表面,保持“和局”,且逐步演变成投降妥协。
1901年9月7日,签订完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的李鸿章,回来后大口地吐血。医生诊断为:胃血管破裂。李鸿章伏在病榻上颤抖地给朝廷写下最后的奏章,也是他生平外交思想的最后总结:
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今议和已成,大局少定,仍望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
在黄河岸边的辉县,从陕西回銮的路上读到李鸿章这份奏章,“太后及帝哭失声”。千疮百孔的大清朝,从此失去了最后可以依赖的一根柱石。李鸿章一生的“政治公敌”梁启超在听到他逝世的消息后,怀着“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的复杂心情,很快写出皇皇大著《李鸿章传》,其开篇即说:“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
李鸿章对于自己的“裱糊匠”身份其实早已洞悉,正如他自己所言,只能抱着“尽一分心酬圣主,收方寸效作贤臣”的态度,疲于奔命,竭尽全力,作为清王朝的忠实奴仆结束他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