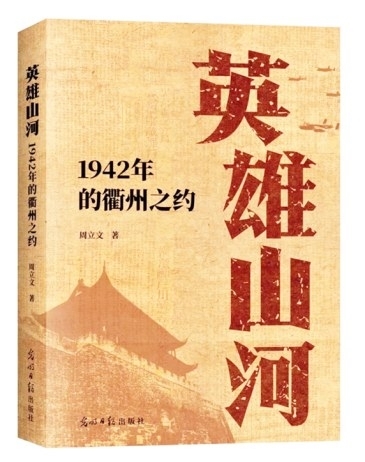
周立文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2025年8月出版
1938年8月,沙汀与何其芳、卞之琳同行从成都去往延安。11月,沙汀跟随贺龙军队前往晋西北、冀中等地搜集写作材料。次年4月,沙汀结束为期半年的前线之行回延安,随后返回家乡四川。纵观沙汀的整个创作生涯,他的文学成就主要来自“返乡”后蛰居四川安县的“雎水十年”。
实践报告文学
抗战爆发后,报告文学逐渐变成一种战时必然的文学形式。对于在战前已经写出不少现实主义小说的沙汀而言,奔赴延安和前线有主动贴近抗战现实、进而实践报告文学的意图。
然而,尝试新的文学形式并非易事,沙汀也遭遇了难题和挑战。《随军散记》就是一个具体生动的案例。它是沙汀力图为贺龙作传的一部长篇报告文学,以叙述人“我”的见闻来塑造贺龙激情豪迈的抗日英雄形象。然而,在英雄之光的暗处,叙述人“我”所面临的生活、写作的难题也逐渐凸显出来。沙汀曾向贺龙吐露过这一困境,贺龙当即宽慰:
同志!到了目的地就好了呀!那个时候还愁没有你们的工作?多得很!四面八方都是材料,恐怕你们两只手也来不及写!行军当中是只好这样呢:走路,吃饭,睡觉!……
“走路”“吃饭”“睡觉”是沙汀在前线的真实处境,也是他写作的难处所在,他面临的问题显得隐秘、琐碎:
昨晚彻夜未眠。刚一迷糊,就看见血肉模糊的尸体,很快又惊醒了。
夜里睡不着,白天也睡不着,一天就这样昏昏懂懂地过去了。
虽然他跟随贺龙先后转战、移防晋西北和冀中平原,搜集了大量材料。但如何及时地用报告、通讯等形式对这些材料进行加工,反映抗战现实,对沙汀而言无疑是一个更大的难题。事实上,沙汀在返川后总结创作经验时,便称《随军散记》等作品为“似报告非报告的小书”。
遭遇无法克服的难题
值得注意的是,沙汀此时虽遭遇报告文学的“难产”,却写下以四川乡镇为背景的著名短篇小说《联保主任的消遣》。以文学遥遥凝视四川后方,体现了沙汀延安经验的“回心”。
沙汀的“脱离”颇有意味,《联保主任的消遣》以“消遣”为主题实际反映的是沙汀“反消遣”的思考,可视为作家现实主义创作观深化的产物。在去延安之前,沙汀就已经有计划以“堪察加”为大标题进行系列小说的写作,试图通过“堪察加”系列将他“所看见的新的和旧的痼疾,一切阻碍抗战,阻碍改革的不良现象指明出来……”
《联保主任的消遣》作为“堪察加”系列的代表作,集中体现了沙汀对“消遣”主题的思考。经由这一拒绝消遣的心理诉求,沙汀建构起对前线生活、写作的想象,这使得他对自己在前线所处的位置及意义十分敏感:
深感自己在这队伍中是陌生的,消息太不灵通,失掉眼睛和耳朵了。
屋子大而空洞,置身其中,感觉自己恰如囚犯一样……因为我们既没有具体工作,也不了解敌我情况,每天就杂乱无章地吃、喝、睡眠和行军……
随军作家如何调整自身位置去动态地贴近抗战、融入陌生的生活,是沙汀遭遇的无法克服的难题:
虽然我看见了一些敌后的新的情况,接触了一些已经有着新的观念和新的感情的人民,并且得到了一般的概念,然而他们原来怎样?其间经历过如何的过程?这一切我都不很清楚……
“无事可作”的随军生活与无法下笔的无聊消遣,构成了沙汀自身紧张而富有张力的认知方式:“其芳说他很爱北平的夏天:有槐花,黄的,还有鸣叫不已的蝉声……而我怀念的却是四川的社会情态,没有多少诗意。”
开掘“狭小而深入”
1939年底,沙汀动身返川。此后,他的小说主要以川西北乡镇为书写对象,在他看来,对后方的“暗影加以暴露,加以讽刺,还是在要求改革,并不是消极的。”他不再满足于记录被时代潮流裹挟的“浮面”,宁愿在乡土地方探索“狭小而深入”的现实主义文学。从返川后的第一篇小说《磁力》到《在其香居茶馆里》《淘金记》等经典,正可追踪沙汀现实主义创作的深入轨迹。与写《磁力》差不多同时,沙汀有感而发:
我不打算接触更多的生活,但我却愿意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看的更深一点,更久一点。与其广阔而浮面,倒不如狭小而深入,这是我的一点成见。
他已经明确的是,前线生活相较自己熟悉的川西北虽广阔却失之于“浮面”。对“狭小而深入”的看重,促使他反思那种“单用一些情节,一个故事来表现一种观念,一种题旨的方法”。在此背景下,沙汀迎来创作高峰,《在其香居茶馆里》《淘金记》等精彩之作也应运而生。
蛰居“雎水十年”间,沙汀创作出了国统区文学的重要实绩。然而,他在战时返乡问题上也遭受质疑。沙汀晚年将之归结到自身所持有的一种“甘居中游”的思想,又提及在重庆学习《讲话》时,周扬曾来信劝说他重返延安或敌后,他自认在回信中说了选择“‘退而求其次’的昏话”。这是沙汀的自省,但也有自辩的意味。时过境迁,再考察他所坚持的“退而求其次”,实则是基于个性特质,尤其是自身文学观念不断发展而作出的理性抉择。
(摘自《文学评论》2025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