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0年8月,《张家旧事》出版座谈会。左前起:汪家明、徐城北、叶至美、叶至善、范用。右前起:沈峻、叶稚珊、曾蔷、黄宗江、董秀玉、杨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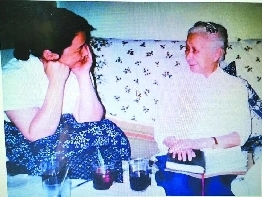
叶稚珊听张允和讲张家旧事
收到快递,是书,汪家明的《范用:为书籍的一生》。范老走了整整13年了,今年百岁。这本书,拿起,就放不下了,因为太多熟悉的名字,勾起一幅幅遥远、沉重、轻快、幸福的回忆……
托付给沈家的“终身事”
家明书中有一章的标题是“《寥寥集》——新的消息”,这个标题让我眼前一亮,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让我先读。
《寥寥集》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沈钧儒先生唯一的一部诗集,由他的三子沈议(叔羊)先生编。诗集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由韬奋先生促成,已出版过三次。40年后,范用先生慧眼识书,他亲自填写了《寥寥集》的发稿单,在编辑过程中又与沈叔羊先生通了许多封长信。
叔羊先生是画家,夫人华庆莲是北京24中的英文教师。一儿一女名宽、松。女儿沈松,与我是中学同班最要好的朋友。当年,我们一同赴陕北插队,极度营养不良染病先后返京。我父母全家去了河南太康五七干校,留我一人托与沈家关照。沈家人只要在我家楼后不用太大声地呼唤一声,我就会应声下楼转去沈家。沈家家里做了稍好一点的饭菜一定叫我。
养好病,我去河南干校投奔父母,松松在北京安排了普通的工作,每年只有探亲回来能聚聚。叔羊先生与我通信,有诗作也会寄给我。
那年回京探亲的一个周末傍晚,沈伯母在窗下唤我,说是请我去她家玩玩。沈宽性格外向开朗,社会上各种朋友交往了不少。晚饭后一屋子“身份不明”三教九流的朋友神侃沙龙,一周少说有两三回。他们很愿意我和沈松两个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女孩旁听。这次见到了一位的确良衬衫领子上有补丁的高个子“叔叔”。原来是徐盈和子冈为他们那已过而立无处安放的儿子(徐城北)焦心,想起拜托衡山(沈钧儒)先生后人。可巧我的父亲也暗自将我的“终身事”托付沈家。于是我们两个“三无”(无学历,无户口,无工作)人员便有了以后的连理终身。
周有光、张允和先生的家,是我的“港湾”
周有光、张允和先生在朝外后拐棒胡同的家,是我的“港湾”。听周老讲“大事”,听允和先生讲“小事”,是享受!周老晚年也是听力不好,外人求他办事,约稿、采访、出书、签合同,他只会“好的,好的!”允和先生客人来,让他离开书桌,他便听从安排,“敬陪末座”。允和先生说:“我给你们讲个笑话……”讲完大家都笑。然后周老说:“我也给你们讲个笑话……”讲完大家更笑。原来他们讲的是同一个笑话。
允和先生有11个小账簿,所有收入支出都记得清清楚楚。她送给我小账本,告诉我:“女人一定要学会记账。”她脑子里还另有本账,每年我的生日、我先生城北生日、我女儿的生日,她都一定送红包。你不能推辞,数目有零有整:城北59岁生日,红包59美元。她说:“你的女儿要结婚,一定要先让我看看,我看过了以后才能同意嫁给他。”结果这仙界的月老倏然仙去,一切没了下文!
《张家旧事》的出版,缘于一次我和城北陪家明看望两位老人。允和先生一如既往地说个不停。当时家明正在为他创意出版的《老照片》倾心尽力,就想看看家中存留的老照片。豪爽的允和先生留饭之后径自搬出历经劫难的家中所存的照片让我们随意翻看,然后去午休了。记得当时家明安安静静听我们谈话,斯斯文文翻检照片。忽然很认真地问我能不能由张允和讲述,我来整理成一本书,是商量的口气。我素来懒散,又要坐班,他也由着我,只在信中顺便一句“此书还拜托您帮忙早日做成”。从创意策划、书名、设计到所分章目、配图都是他一手经办。
1998年《张家旧事》出版,多次加印,那时这种文体的书籍还少,了解张家四姐妹的人也不多,有人戏称这本书引爆了张家文化的研究。但书成后,知道我的人多,知道他应头功的人少。其实这本书一大半的辛劳应该归于他。
从《张家旧事》又想到《水》,本是20世纪30年代张家姊弟在苏州九如巷自办的家庭刊物,自娱而已。60年后,张允和、兆和又在后拐棒胡同复刊。约稿、编辑、打印、复印、装订,花费了两位老人多少精力!允和先生为此在84岁上决心学习使用电子打字机,她不会汉语拼音,口音又“半精(京)半肥(合肥)”,硬是一个字一个字查字典注音,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当然是全程指导。筹划了两年,1995年10月28日,张允和向海内外的张氏家族成员发出了第一封约稿信,给在苏州的寰和五弟的信的开头是“最最亲爱的小五狗……”
似是旧人来
高高大大的叶至善先生自从被河南潢川五七干校“放回来”以后,曾常来我们西四北的小院。叶圣陶先生当年办《中学生》,牵起了我的公公婆婆一生的姻缘。公公徐盈长至善先生五岁,兄友弟恭,客气亲切。
家明的书中记下了范用和至善先生在东四附近的小馆约饭的趣事,叶至善给范用写过一封短信:
中午11时25分,我去到“孔乙己”,等到12点10分还不见人来,只好要了四样菜一瓶酒,独自喝了起来。在酒店里独酌,回想起来还是头一回,也别有风趣。可惜心里总不踏实,大概是我记错了日,你约我星期六,我误作星期日了。应邀而不见面,真有点荒唐,抱歉之至,好在以后有的是机会,不必放在心上。
在民盟中央工作时,一次统战部开会需各党派参会人员事先定准以便准备桌签,电话中人事部门报上我的名字,统战部的同志有些为难地说:“叶老那么大年龄不要惊动他了吧……”后来知道因为名字的发音几乎相同,又都是党派的成员,多少次引出误会。
1999年8月,《张家旧事》出版座谈会,叶至善、叶至美、黄宗江、范用、张中行、姜德明、董秀玉、沈峻等前辈都来了。在门口叶至善笑着对我说:“我们的名字同音不同字,我很惊奇,看了你《张家旧事》写的序言和为《最后的闺秀》写的后记,就知道你很会写东西……”我愧不敢当!作为晚辈,这是我和至善先生唯一的一次交谈。
家明的书中摘引了范用和罗孚的几封通信,恰巧我也还记得那些年罗孚先生的境况,现在才知道,在多少熟人旧友对他避之唯恐不及的日子里,范用先生给了他那么真诚的温暖。范用先生的夫人丁仙宝在原单位退休后曾被请到群言出版社帮忙会计工作。回想起来丁仙宝先生从不爱出头露面,勤勉简朴,一丝不苟,身着旧衣伏案不语,下班匆匆离去的背影是留给我的最后印象。2000年夫人仙逝,范用先生竟跪地痛哭:“她对我太好了,她也是我的妈妈。”范用在给罗孚先生的信中说:“老伴长我三岁,我19岁见到她,次年结缡,70年恩爱到底,我一生幸福……”可惜“为书籍的一生”的范用先生,没有写下一篇详叙追忆终身伴侣的文章。 (摘自11月12日《新民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