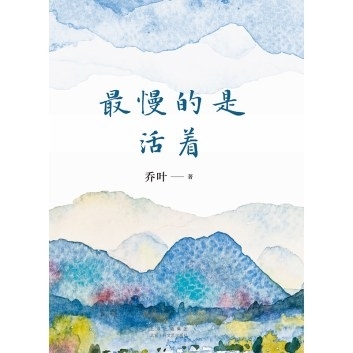
乔叶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4年1月出版
本书包含《最慢的是活着》《叶小灵病史》《给母亲洗澡》《明月梅花》四篇小说。《最慢的是活着》从年轻一代女性“我”的角度审视奶奶那一代女性的一生,从质疑、理解到超越。《叶小灵病史》讲述的是叶小灵的“城市梦”。《给母亲洗澡》讲述的是给母亲洗澡的女儿如何一点一点地洗出母亲的过往,母亲的身体史,其实就是她的生命史。《明月梅花》讲述的是流淌在三代人之间的血脉亲情。四篇小说聚焦亲情、女性成长等,乔叶创作的鲜明主题,创作时间从2008年延续至今,能够直观展现乔叶小说创作的成长脉络。
妈妈患的是脑溢血。症状早就显现,她因为信奉主的力量而不肯吃药,终于小疾酿成大患。当她出院的时候,除了能维持基本的吃喝拉撒之外,已经成了一个废人。
妈妈病情稳定之后,我向报社续了两个月的假。是,我是看到她和妈妈相依为命的凄凉景象而动了铁石心肠,不过我也没有那么单纯和孝顺。我有我的隐衷:我刚刚发现自己怀了孕。孩子是我最近一位男友的果实,我从北京回来之前刚刚和他分手。
我悄悄地在郑州做了手术,回家静养。因为瞒着她们,也就不好在饮食上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和要求。三代三个女人坐在一起,虽然我和她们有十万八千里的隔阂,也免不了得说说话。妈妈讲她的上帝耶稣基督主,奶奶讲村里的男女庄稼猪鸡狗。我呢,只好把我经历的世面摆了出来。我翻阅着影集上的照片告诉她们:厦门鼓浪屿、青岛崂山、上海东方明珠、杭州西湖、深圳民俗村和世界之窗……指着自己和民俗村身着盛装的少数民族演员的合影以及世界之窗的微缩模具,我心虚而无耻地向她们夸耀着我的成就和胆识。她们只是默默地看着,听着,没有发问一句。这在我的意料之中。我知道自己已经大大超越了她们的想象——不,她们早已经不再对我想象。我在她们的眼睛里,根本就是一个怪物。
讲了半天,我发现听众只剩下了奶奶。
“妈呢?”
“睡了。”她说,“她明儿早还要做礼拜。”
“那,咱们也睡吧。”我这才发现自己累极了。
“你喝点儿东西吧。”奶奶说,“我给你冲个鸡蛋红糖水。”
这是坐月子的女人才会吃的食物啊。我看着她。她不看我,只是踮着小脚朝厨房走去。
报社在河南没有记者站。续假期满,我又向报社打了申请,请求报社设立河南记者站,由我担任驻站记者。在全国人民过分热情的调侃中,河南这种地方一向都很少有外地人爱来,我知道自己一请一个准儿。果然,申请很快就被批准了,我在郑州租了房子,开始了新一轮的奔波。每周我都要回去看看妈妈和她。出于惯性,我身边很快也聚集了一些男人。每当我回老家去,都会有人以去乡下散心为名陪着我。小汽车是比公共汽车快得多,且有面子。我任他们捧场。
对这些男人,妈妈不言语,奶奶却显然是不安的。开始她还问这问那,后来看到我每次带回去的男人都不一样,她就不再问了。她看我的目光又恢复到了以前的忧心忡忡。其实在她们面前,我对待那些男人的态度相当谨慎。我把他们安顿在东里间住,每到子夜十二点之前一定回到西里间睡觉。奶奶此时往往都没有睡着。听着她几乎静止的鼻息,我在黑暗中轻轻地脱衣。
“二妞,这样不好。”一天,她说。
“没什么。”我含糊道。
“会吃亏的。”
“我和他们没什么。”
“女人,有时候由不得自己。”
似乎有些谈心事儿的意思了。难道她有过除祖父之外的男人?我好奇心陡增,又不好问。毕竟,和她之间这样亲密的时机很少。我不适应。她必定也不适应——我听见她咳嗽了两声。我们都睡了。
日子安恬地过了下来。这是我期望已久的日子:有自由,有不菲的薪水,有家乡的温暖,有家人的亲情,还有恋爱。在外奔波的这几年里,我习惯了恋爱。一个人总觉得凄冷,恋爱就是靠在一起取暖。身边有男人围着,无论我爱不爱他们,心里都是踏实的,受用的。虽然知道这踏实是小小的踏实,受用是小小的受用,但,有总比没有要好。
“没事不要常回来了。我和你妈都挺好的。不用看。”终于有一天,她说。
“多看看你们还有错啊。我想回来就回来。”我说。
“要是回来别带男人,自己回来。”
“为什么?不过是朋友。”
“就因为是朋友,所以别带来。要是女婿就尽管带。”她说,“你不知道村里人说话多难听。”
“难听不听。干吗去听!”我火了。
“我在这村里活人活了五六十年,不听不中。”她说,“你别丢我的人了!”
“一个女人没男人喜欢,这才是丢人呢!”
“再喜欢也不是这么个喜欢法。”她说,“一个换一个,走马灯似的。”
“多了还不好?有个挑拣。”
“眼都花了,心都乱了。好什么好?”
“我们这时候和你们那时候不一样。你就别管我的事了。”
“有些理,到啥时候都是一样的。”
“那你说说,该是个什么喜欢法?”我挑衅。
她沉默。我料定她也只能沉默。
“你守寡太多年了。”我犹豫片刻,一句话终于破口而出,“男女之间的事情,你早就不懂了。”
静了片刻,我听见她轻轻地笑了一声。
“没男人,是守寡。”她语调清凉,“有了不能指靠的男人,也是守寡。”
“怎么寡?”我坐起来。
“心寡。”她说。
我怔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