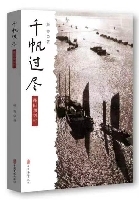
《千帆过尽:鄱阳湖别传》 赵青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2024年2月出版
在古代农耕文明时代,鄱阳湖曾叫“彭蠡湖”,一度成为江西山水地理和地缘地理的代名词。本书从“彭蠡”这个点切入,围绕鄱阳湖的“源头”“通道”“迁徙”“渔家”“绝唱”“兵家”“鹤乡”“风情”“裂变”“汇流”娓娓道来,构成一个烟波浩淼的大湖印象。
赵青老师生在都昌,我生在永修,两家隔着鄱阳湖,都隶属九江。用他的话来说,鄱阳湖涨水时我们的村子就都属于鄱阳湖了。此话不假,记忆中1983年的那场大水,鄱阳湖里的大鱼是可能游到我家厨房的。
认识赵青老师是上世纪80年代末的事情。当时我还只是云居山脚下的一位高中生,终日游游荡荡,时而逃学上山。由于热爱文学的缘故,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我背着一部手写的诗稿和两个从食堂买来的馒头,独自去近百公里外的九江日报社投稿。那个遥远的夏日,我们在编辑部聊了好一会儿,具体内容早已模糊不清,不过有个细节却一直记得。那是在临走的时候,赵青老师将我送到编辑部大门外,在说了几句鼓励的话后,又转过脸对身旁的阳小毛说,“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那时候还沉重啊!”
为什么像我这样的年轻后生当年给赵青老师留下的印象首先是“沉重”二字呢?而在中学同学眼里我幽默、开朗,壮志凌云。可赵青老师是对的,因为他直接接触到的是我的文字,里面不仅潜藏着我与生俱来的某种气质,同样沾染了80年代文学特有的忧郁……
至今我没有追问过赵青老师是否选刊了我的某篇沉重的诗稿,其实他也早已忘了我这个芸芸众生中的投稿者。我的最大收获在于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并且从一位素昧平生的长辈那里听到我有一种深藏于内心的忧郁气质。因为文学的缘故,我没有因此感到沮丧或懊恼,相反这样的评价在我的内心引起了共鸣。事实也证明,始于当年的激情与忧愁,如同我对文字的热爱本身,将对我的一生影响深远。
言归正传。当赵青老师邀我为《千帆过尽:鄱阳湖别传》写序,我自知这实非我之所长,任何简单赞美或批评对我都是艰难的。在九江的日子,从茶馆、寺庙到风景,许多事物着实让我印象深刻,而最让我感动的就是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对我的呵护以及对本乡本土的热爱。赵青老师这些年来的写作多与这片土地有关,而这次有关鄱阳湖及其周边风土人情与地理、历史的梳理,虽然书中更在意的是资料性而非文学性,同样清晰可见的是其在“为故乡立传”方面所做的巨大努力。
在书中作者特别谈到一种在野的状态,而鄱阳湖及其周边无疑有着不负盛名的江湖之远。在写到洪范时,有段话读来感人至深:
一个人,来到世间,就像一片树叶挂在寒风里,独自构成一个存在空间。谈论他的时候,他已经从树叶上飘下来,追随寒风而去。曾经见过他的人,偶尔会想起他。这种想起,因为是虚拟的,并不代表真的是那么回事。很多的时候,人们会想起某首已经消失的诗或者某幅已经消失的壁画,但你永远不知道那首诗的语言,那幅壁画的真实面貌,树叶被尘土掩埋了,新的植物长了出来,世界被新的生命替代,逝去的人给世界一个永久沉默的空间。
想象此刻在鄱阳湖边仰望星空,我们整个人类在浩瀚宇宙又何尝不是处于一个在野的状态呢?然而,人还是会一边想象自己是宇宙的中心,一边寻找若有还无的家园。和大多数人一样,我也总在故乡与天涯之间拉锯。一个我说“走不出去的地方是人生的滑铁卢”,另一个我则永远想着回到故乡的山坡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