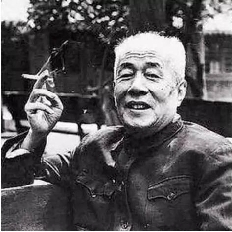
·黄萌生·


鲁迅赠款
我的父亲黄廷珦(1915-2001,见左图,父亲与我在河南大学门口)出生于南阳内乡一个士绅家庭。1932年,黄廷珦到北平读书。1934年春,又到上海投亲,当时上海也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黄廷珦在上海见到了同乡诗人、左翼作家杜谈,杜谈在北大做旁听生时与黄廷珦熟识。杜谈1930年加入北平左联,参与编辑进步刊物,同时发表诗作,1932年到上海,与蒲风等发起成立中国诗歌会,主持《新诗歌》的编辑出版。
老乡见面谈得最多的却是鲁迅。杜谈于1929年5月与王正朔、王冶秋等在北大不止一次听过鲁迅的演讲,鲁迅的著作他也差不多集齐并全读过。他说自己来上海两年了,一直想去看望他最崇敬的先生,当面请教一些问题,但唯恐打扰和麻烦先生,就以窦隐夫的笔名写信征求鲁迅对新诗歌的意见,不久先生便回了信。黄廷珦听说杜谈有鲁迅亲笔信,便如获至宝地读了起来。在信中,鲁迅就有关新诗歌的形式问题,提出了精辟见解,回信中还有这样两句话:
我不能说穷,但说有钱也不对,别处省一点,捐几块钱在现在还不算难事。不过这几天不行,且等一等罢。
不久,鲁迅托徐懋庸转赠《新诗歌》杂志30元钱。杜谈将这封回信和当时通用的六张五元纸币,交给黄廷珦保存。黄廷珦双手微微抖动着,似乎那信、那纸币还带着先生的体温,带着他16岁时在阴冷风沙天感到的暖意。后来杜谈取走钱供杂志急用,那封珍贵的信则一直由黄廷珦小心珍藏,后因杜谈突然失联(被特务抓捕,后奔赴延安),黄廷珦在离开上海时将信转交亲戚保存。
石刻汉画
1935年秋天,黄廷珦返回南阳,一下车就直奔杨家大院。杨家大院在南阳赫赫有名,是教育家杨鹤汀的府第,杨鹤汀曾任民国首任南阳知府。他的大儿子杨廷宝是中国建筑史上泰斗级人物,与梁思成并称“南杨北梁”;二儿子杨廷宾,此时在南阳女中任美术教师,性格沉静刚毅,气质温文尔雅,一身“洋装”颇有上海明星的文艺范儿。王正朔与杨廷宾是战友,常出入杨家。王正朔在有“小抗大”之称的南召现代中学教书,每每回南阳便吃住在杨家。外人想不到的是,这座名流出入的杨家大院,竟是南阳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站。
黄廷珦与王正朔、王正今、杨廷宾等相会,久别重逢,分外亲热,并受到王正朔结结实实的一个拥抱。他们七嘴八舌地问:上海时局怎样?有没有党组织活动的线索?是否见过鲁迅先生?黄廷珦一一回答,最后说他在内山书店见过鲁迅一次,但不好冒昧当面请教,错失良机,恐怕要遗憾终生。
王正朔说:“廷珦,你不必遗憾。”然后他又略带神秘地说:“我和老五(杨廷宾)正为鲁迅先生做一件大事。”他见黄廷珦十分急切又好奇,就直透谜底:“我们受台静农和老三(王冶秋,见中图)之托,正筹划为鲁迅先生拓印石刻汉画。”
原来,老三王冶秋在北平出狱后,相继结识了韦素园、台静农等新文化运动干将。一次,他们三个去西城阜成门内西三条二十一号鲁迅住处请教。可能在鲁迅看来,王冶秋只是个未谙世事的半大小子,就给他端了一盘瓜子,安排他在南屋看书。机灵的王冶秋开着门,偷听他们商谈办刊大事。鲁迅谈了办刊宗旨:“批评社会、批评文明”,以及写文章要“率性而言,平心立论,忠于现实,望彼将来”。这席话让王冶秋豁然开朗并受益终身。
那个以长矛匕首投向敌人营垒的无畏战士,怎么关心起这毫不起眼的汉画石刻了呢?看到黄廷珦意外的表情,王正朔解释道:“鲁迅先生可不是单纯玩古,是为了继承中华祖先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取其精华,教育民众,开创远超过去的更新更美的新文化,这也是一大战斗任务啊。先生说,未来的光明前景将一定证明,我们不仅是文学艺术遗产的继承者,也是新文艺的建设者和开拓者。”
鲁迅对祖国文化遗产一向极其重视,并对南阳汉画像石心向往之。台静农在北平为他搜集像石拓片,曾问他是否见过南阳汉画拓片,他回信说:“南阳画像,也许见过若干,但很难说,因为购于店头,多不明出处也。倘能得以全份,极望。”一个殷切的“极望”,使得在北平的台静农和在山西的王冶秋分别写信给南阳的好友杨廷宾,引出南阳年轻共产党人在进行地下斗争的同时,为鲁迅搜集南阳石刻汉画(见右图,鲁迅收藏的汉画像石拓片)的一段佳话,也使南阳汉画这一宝贵艺术重见天日并大放异彩。
当时南阳一带少有现成的汉画拓片,王正朔、杨廷宾、王正今他们深入南阳一些县乡村镇,发现了不少有价值的刻石,可惜这些艺术珍品多遭冷遇,有被扒毁的墓石、房基、桥柱、饭桌、石凳、脚踏石等,皆弃置于郊野,遭战火风雨剥蚀,濒临毁灭。他们在一农家猪圈里,发现了一块满是粪便的汉石,用泉水冲洗干净,斑驳的图案清晰展现,杨廷宾惊叫道:“这不是一只太阳鸟吗?金鸟驮日,自由翱翔,多浪漫多丰富的想象啊!”他们心疼又心急如焚,可那个时代,那种环境,那么多濒临消亡的宝贝,他们又能如何呢?
当黄廷珦再次到南阳小住时,杨家大院正一派繁忙。一间大屋里堆着一沓沓从武汉购进的连史纸,几位南阳闻名的捶印碑帖的老师傅,带领五六个年轻徒弟,穿着毛蓝土布大褂,吃住在杨家,日夜操劳。拓工们白天由王正朔、杨廷宾引领,按原先搜寻计划的路线,到各县山野村镇奔波拓印,夜里在院里将拓片晾干,然后精心挑选,整齐包装,寄往上海。
杨廷宾一脸得意,让黄廷珦欣赏还未包装的拓片。仅仅数十帖,黄廷珦已看到了或凝重典雅,或浪漫飘逸,或简洁灵动的各种场景图案。的确,王正朔、杨廷宾请来的是南阳顶尖的拓制高手,他们惜墨如金,一张拓片由大小拓包无数次捶拓而成,不洇,不透,达到准(准确反映原石信息)、匀(用墨均匀无污点)、净(边缘干净整洁)的标准,而且捶拓手法因石刻而异,有时用墨轻淡,薄如蝉翼;有时捶墨浓厚,重如乌金。这样的汉画拓片,本身就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
喜爱之情
一天中午,黄廷珦他们在杨家吃饭。杨廷宾一脸兴奋地说:“王冶秋来信说,鲁迅先生嘱托要请好的拓工拓印,要用好纸好墨。我把上次拓印成的十幅拓片样品,寄至山西由王冶秋转寄给鲁迅先生。先生收到后非常高兴,还给我写信,说他对拓片的内容和拓印的质量表示满意。还指示如何注明拓片印石的出处及发现年月,即要注写在每张拓片下角空白处。先生对咱们的工作表示致谢并赞扬有加。”
王正朔风趣地对黄廷珦说:“花钱、管饭,请有名的拓工,派人到汉口买好纸好墨都没问题,我是总参谋长兼外交大臣,杨廷宾是内务兼财政大臣,重要的是,咱们有内阁总理的英明领导和大力支持,什么事情都不难办了。”他指着杨廷宾的父亲杨鹤汀,伸出大拇指。坐在上首的杨鹤汀,捋着飘飘银须,呵呵地笑了。
王正朔、杨廷宾他们从1935年秋至1936年鲁迅逝世前两个月,先后为鲁迅搜集拓印的汉画像石拓片有241幅。鲁迅对拓片的喜爱之情,在日记中多有记载。
1935年12月21日,鲁迅在写给台静农的信中说道:
南阳杨君,已寄拓本六十五幅来,纸墨俱佳,大约此后尚有续寄。将来如有暇豫,当并旧藏选印也。
在同一日给王冶秋的信中又云:
今日又收到杨君寄来之南阳画像拓片一包,计六十五张,此后当尚有续寄,款如不足,望告知,当续汇也。这些也还是古之阔人的冢墓中物,有神话,有变戏法的,有音乐队,也有车马行列,恐非“土财主”所能办,其比别的汉画稍粗者,因无石壁画像故也。石室之中,本该有瓦器铜镜之类,大约被人拣去了。
1936年夏,王正朔亲自协助拓工将原来选定的魏公桥、七孔桥等多处60多块画像石刻抢在汛期前拓印出来,并将亲著的《南阳汉画像石访拓记》与拓片及一封信一并寄给鲁迅。不久,已是南阳地下党宛属工委书记的王正朔喜出望外地见到鲁迅的回信。
王正朔一直将这封珍贵的信收藏在身边。1937年3月,他由南阳奉命到北方局,将此信从北平寄给在上海的许广平,后编入鲁迅书简影印本中。而杨廷宾收到的鲁迅的信,悉数珍藏在南阳家中,可惜历经战乱,现已荡然无存。
(摘自《名人传记》2023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