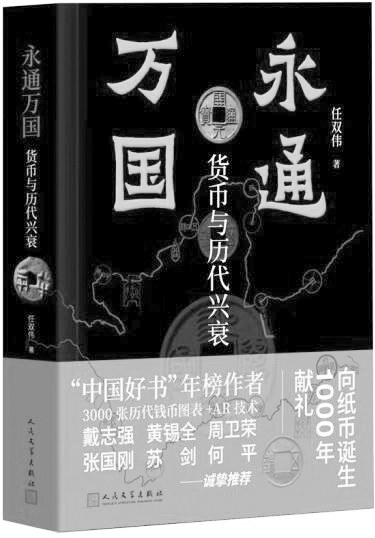
《永通万国:货币与历代兴衰》 任双伟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1月出版
本书梳理了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的货币形态,如贝币、铜钱、纸币、白银等的特征与使用历程,生动形象地叙述了货币发展、货币制度和货币政策对王朝兴衰的影响与作用,从钱币的方孔谛观历史。
货币有何价值?
我一直认为,货币的价值首先是历史学和经济学意义上的,应该是为历史与经济学提供材料,又受之规范,进而达到共荣。如果脱离了历史学与经济学,货币研究将是空中楼阁,将是就材料而材料,对无意义施加意义。
中国钱币学的发展源远流长,早在1500多年前的南朝梁之时,就出现了顾烜的《钱谱》,出现了以历史实物为研究、收藏对象的学术活动。这一情况,远远早于西方世界。
从经济角度来看,货币的长期稳定,说明了经济的繁荣。沉醉于版目繁多的钱币专家们希望所见、所过手的钱币越多越好,虽然不是说他们希望国家经济生活恶化,钱币发行混乱与多样,可实际上,这种多变与动荡,哺育了许多钱币收藏爱好者,使他们发生长久的、历史的、收藏的、文化的产生对钱币收藏的兴趣。
对于新莽、徽宗钱币的追求,则多源于他们的艺术性,艺术的审美追求标新立异、别具一格,而生活之美则追求恬静、安宁、普通,钱币收藏者对钱币艺术的追求本质上是对生活之美的厌倦,对个性之美、超越之美的追求,是一种人格的内在表演。
至于史学与钱币学。钱币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和史学分道扬镳的?我个人认为,无论是中西,都是在 17、18 世纪,即博学时代和乾嘉考据时代。
长期任教于牛津大学的莫米利亚诺曾有此感慨:“我一生都对一种人特别好奇,他们与我的职业相近,我可以清楚地知道他们的志趣,也能分享他们的热诚,可他们的最终目标,又让我感到神秘莫测。这一种人对历史的事实充满兴趣,却对历史学本身兴味索然。”莫米利亚诺认为这些古代的历史研究者,在近代前夜,都走向了与历史学的分化之路,他们都成了收藏家,或者人类学家。
其实博学时代和乾嘉考据时代都是一种皮浪主义。前者的斗争对象是中世纪神学,后者的对象是宋明理学。早在博学时代之前的文艺复兴初期,博学派的研究已经带有很强的复古性,他们借用古代希腊和罗马之古,对神学进行从头到尾的批判。瓦拉以文献学为突破点,在《〈君士坦丁堡赠礼〉伪作考》中运用文献学的技术,揭穿了“丕平献土”的骗局,动摇了教皇统治的合法根基。
清儒对宋明理学空泛的理论感到厌倦,在内容和方法上释放了传统儒学尤其是汉学、唐代儒学的知识,以至于凡文字、音训、校雠、辑佚、天文、历算、医卜、水利、金石都成了专门之学。而清初学者胡渭的《易图明辨》,也让宋明理学视为根基的《河图》《洛书》成了无源之水。
再后来,西方兰克确立的政治史规范和中国贯通日久的“经”学传统,让钱币等古物显得格格不入,不得已之下,终于形成了专门化的新途。让钱币从史学的附庸地位中解放出来,独立成专门之科。由是清代的钱币学家以宋代的古器物学为参照,也形成了自己的一整套著作体系,即《钱谱》,沿袭至今。
博学时代和乾嘉考据时代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就,无限扩大了史料的来源,加深了中西怀疑求真的精神。现代以来,博学家和历史学家又走上了合流之路,这也是基于现代史学的趋势。
就中国钱币学而言,钱币或者说货币的研究也越来越指向了历史学的目的:一是通过发扬古代货币,为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提供实际材料;二是通过探讨货币的变化和运动规律,总结历史经验,吸取教训,古为今用,西为中用,为现代化建设服务。而这两者,都是以历代钱币或者货币的收集、收藏、发掘、清理、整理、展览和交流为根基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在过去的几十年,钱币界似乎更加重视基础的建设,而忽略了钱币价值之阐发,走向了与历史分裂之纵深之途,而忘了来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