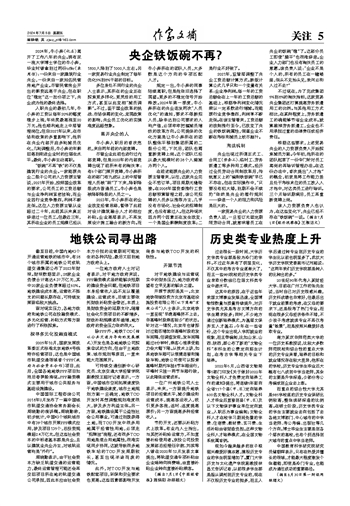2024年,牛小奔(化名)离开了工作八年的央企。拥有双一流大学博士学位的牛小奔,毕业时曾拿到过两份offer(录用信):一份来自一家建筑行业央企,一份来自一家知名民营房地产企业。尽管民营房企开出的薪资远高于央企,但在职位“稳定”这一加分项之下,央企成为他的最终选择。
入职央企的最初几年,牛小奔的工资以每年20%的幅度稳步上涨,年终奖最高涨至20万元。他也顺利地走上中层管理岗位。但自2021年以来,在市场和政策的多重影响下,他所在央企内部开启多轮减员优化,几轮调整后,牛小奔的年薪回落到刚进企业时的应届生水平。最终,牛小奔主动离职。
“饭碗”不再“铁”的不仅是建筑行业的央企。一家能源央企二级子公司的人力资源主管说,2021年开始,按照国企改革的要求,公司员工的工资总额与企业净利润紧密挂钩,而企业因行业竞争激烈,利润不断走低。这位人力资源主管从业超过二十年,此前其从未真正辞退过一位员工。但最近三年,其所在企业的员工规模已经从1800人降到了1000人左右。另一家贸易行业央企制定了每年优化5%到8%干部的目标。
多位身处不同行业的央企人士表示,其所在的企业正在探索更多样化、更灵活的用工方式,甚至以此变相“减员调薪”。不过,鉴于国企改革的挑战、市场供需的变化、宏观政策的影响,央企员工优化的实操难度远超想象。
离开央企的人
牛小奔入职后的首次危机,来自两年前的内部竞聘。
尽管企业此前也进行过内部竞聘,但是2022年的内部竞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淘汰率:有6个部门展开竞聘,牛小奔所在的部门有九成以上的中层管理人员被“刷”了下来,降职降级成为普通员工。牛小奔也是被降职降级的人员之一。
2023年,牛小奔所在的企业改变经营思路,暂停了此前对设计建筑融合人才的相应补贴。企业高层表示,不再发展设计施工融合的新方向。而牛小奔所在的团队人员,大多数是这个方向的专项匹配人才。
规定一出,牛小奔的同事陆续离职,但是他依旧选择了观望。更多的不稳定信号开始释放。2024年第一季度,牛小奔所在的央企连发两次“人员优化”的通知,要求不得新招人员,除非达到公司要求的人均产值,必须牢牢把握减员增效的改革方向。公司提供的优化方案是让牛小奔所在的团队整体平移到集团所属的二级分公司,下沉后,团队也需重新竞聘上岗。这个团队已经从最大规模时的38个人缩减为两个人。
在前述能源央企的人力资源主管看来,以往,这家央企完全不愁订单,项目周期无缝衔接。在2008年国资委推行工资总额预算管理之前,该公司招聘的人员多以推荐为主,几乎没有市场化、社会化的招聘制度,也没有裁过人。但这种现状因为两个因素正在发生改变:一个是国企薪酬制度改革;二是行业不好做了。
2021年,监管层调整了央企工资总额计算方式。新版计算公式几乎只和一个变量有关系:企业净利润。每一年的工资总额会在上一年的工资总额的基础上,根据净利润变化情况乘以一定系数进行增减。而能源行业竞争激烈,利润率不断走低。在该主管看来,工资总额的改制推行至今,已改变了央企的铁饭碗属性,倒逼企业不断在考核和减员上绞尽脑汁。
淘汰机制
央企出现过所谓正式工、合同工(劳务工)、临时工、劳务派遣工等多种用工模式。经历过全员劳动合同制改革后,传统意义上的“编制铁饭碗”早已不存在。但在实际操作中,“只要没有犯大错,到期不会不续约”依然是央企的潜行规则——辞退一个人的阻力和风险是巨大的。
一家贸易央企的人力资源负责人说,一旦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就意味着员工在央企的饭碗“稳”了。这部分员工即使“躺平”也很难辞退。企业人力部门也没有淘汰员工的意愿。该负责人说:“企业不是个人的,所有的员工在一幢楼里,低头不见抬头见,我何必和人过不去?”
不过现在,为了完成集团5%到8%的淘汰指标,这家贸易央企集团还打算提高劳务派遣用工的比例。与其他用工方式相比,在某种程度上,劳务派遣工的确能够节省企业成本。就算裁掉劳务派遣工,企业也不用承担过重的法律责任或经济责任。
根据这些要求,上述贸易央企的人力资源负责人开始探索减员方案。今年初,他所在的团队起草了一份专门针对员工离岗的再培训管理办法。在这份办法中,首次提出“人才池”的概念,初衷是将工作能力差且处于考核末位的员工放入人才池中,对这类员工进行培训。三个月培训期满后,员工再重新竞聘上岗。
该人力资源负责人也认为,在这些变化下,央企已经不存在“铁饭碗”一说。 (摘自7月1日《经济观察报》 王雅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