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左起:徐积锴、徐善曾、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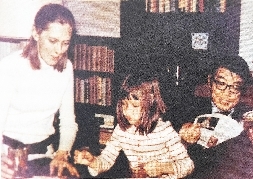
董鼎山与妻女

郁飞、王永庆夫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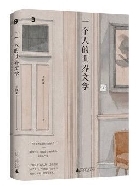
(摘自《一个人的文学世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5月出版)
志摩孙子写志摩
徐志摩之子徐积锴先生跟我闲聊时对徐家后人没有治文艺者感到有些羞赧,他告诉我其子徐善曾学的是理工,读完博士后,他曾经到上海、硖石等地搜集了爷爷、祖母张幼仪和陆小曼的好多资料。
10年前在纽约纪念徐志摩会议上被邀发言,我得遇专程自千里外的加州赶来的徐善曾,那次徐积锴也在,我旋即跟他们父子俩续起了孙子写传记的话题。善曾就读著名的密西根大学,是工程学博士。他记得小时候在上海的房子,记得祖母带他们在上海的往事。
善曾不能忘记爷爷那略带忧郁、像是在发问的眼睛,于是就开始了追摹和跋涉之旅。过去这些年,他到世界各地搜集祖父遗留的资料,追索他学习和生活过以及对志摩的生命和生活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地方。
他告诉我,因为他不谙中文,诸多材料处理起来相当困难,必得假以时日,并希望得到中英文俱佳且又愿意献身其事的助手来共襄此举。其后我们又见过面,徐善曾长得颇肖爷爷徐志摩,但他也有科学家和管理人的历练;我问起他写爷爷传记的事情,他只是微笑,说仍在搜集材料。
没想到,又10年后的今天,徐善曾终于出版了这本书。最近,善曾来纽约参加纪念徐志摩诞辰120周年纪念会,我跟他有缘再会。聊了20年间他写作此书的甘苦和体会,非常感动。
善曾童年生长在上海和香港,虽然年幼,但他对上海和故家有着难以磨灭的记忆。他六岁时移民美国纽约,看到家里挂着祖父徐志摩的照片,总对这个人感到神秘且幽远。直到上大学后,一次有位美国汉学家来校讲徐志摩,学校里仅有的几位华裔学生义务帮忙贴海报。同学中有人打趣说这老美讲的中国诗人与你同姓,或许跟你沾亲带故吧?
没想到他打电话问父亲,这著名诗人居然就是自己的爷爷!这件事震惊并刺激了徐善曾,他想要更多了解自己的爷爷和家世。半个世纪了,那时埋下的种子现在发芽成树了。
只为了搜集材料,他就跑了三个半大洲;除了中国和美国,他还专门跑了英国、法国、意大利和东南亚。旅行不下数万里,采访了无数汉学家、当事人及专家学者;他甚至专程踏访泰戈尔的家乡、勘探他祖父飞机失事的地点等。去过最多的是上海,当然也包括济南、海宁。
所幸,他掌握着绝大多数人没有的独门资料。徐善曾有足够的学术敏感和训练有素的科学精神,所以打开新书仍然资料不少,琳琅满目有新鲜感。他这部写自己爷爷的传记名曰Chasing the Modern。
郁达夫儿媳说王映霞
我在纽约跟郁达夫、王映霞的长子、儿媳郁飞夫妇曾经有过多年往还,得知郁王婚变一些秘辛和第一手资料。
当年王映霞愤然离开新加坡,唯有爱子郁飞陪伴郁达夫。作为第一见证人,郁飞深味父亲的心酸和悲愤。直至新加坡陷落前夜,郁达夫才送爱子郁飞回国,自己坚守在抗日前线。
郁飞此后同样历经磨难,而晚年的王映霞也非常关心自己的长子,为郁飞的际遇感愧和哀伤。为了使自己一生受苦的儿子有个幸福的生活,她辗转求友人、重庆战时宋美龄幼儿园园长刘怀玉老人介绍,郁飞得遇王永庆。郁飞、王永庆终成眷属,其乐融融。
郁飞温厚且讷于表述。所幸其妻王永庆是个“活字典”而且乐于叙旧;她直爽热情,将多年来与婆婆的交往和私语传递出来。王映霞在儿媳面前,屡屡敞开心扉。她谈自己的心迹、谈当年郁达夫的多疑和猜忌,当时的兵荒马乱更给离人添尽千古愁。王映霞在晚年曾多次认真否认并辩解那段误传的恋情和冤情,并控诉世情的险恶毁了他们的婚姻。
王映霞回忆当年她从新加坡离开郁达夫时,只拎了一只小箱子走出房门:
郁达夫也不送我出来,我知道他面子上还是放不下来。我真是一步三回头,当时我虽然怨他和恨他,但对他的感情仍割不断;我多么想出现奇迹:他突然从屋子里奔出来,夺下我的箱子,劝我回去,那就一切都改变了……
据王映霞自述,她此后万念俱灰,只想要一个安定的家。而郁达夫的个性只能跟他做朋友而难做夫妻,所以她与郁达夫最大的区别就是性格上的差异。别离了郁达夫,她只想一生平平安安做个小女人。
记得当年毁家前后,无数名人曾经进行劝说。他们的挚友郭沫若曾经就郁达夫过分暴露隐私、“抢戴绿帽子”而让王映霞难堪替她辩解和申诉过。而且王映霞对传言终生抵死不认。王映霞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后仍然向儿媳辩解清白之身,可见兹事体大。
董鼎山为何娶洋妻
在董鼎山先生的晚年,我曾应邀撰写他的口述史。老爷子是个有浪漫情怀的人,即使90多岁了,谈起风光事仍然不减当年勇。“你们一定想知道我为什么娶洋妻子过了一辈子吧?我不是不想娶中国人,是只能‘望中兴叹’啊!”
他当年在上海滩是当红记者,又兼写海派小说,接触当红影星歌星无数,相貌高大英俊,应该是有无数韵事的。“当年,老是女孩子追我。”可是他在事业和人气的顶峰时,离开上海滩到美国小城密苏里留学。接着,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炙手可热的留学生一下子成了政治难民。特别是,这些人已经到了适婚年龄,甚至超龄。跟董鼎山差不多同龄的唐德刚先生在忆当年时写道,那时曾流行于留美学生间的理想目标是:洋车洋房、洋女为妻!
我猜想董先生可能是这个口号的践行者。“完全不是!”没想到老爷子断然否定,“我那时候是不敢追求中国女孩子啊!”他说道:你想想,当年中国人能留学该多么稀罕,特别是女留学生。她们大多是达官显宦或暴富新贵的女儿,每天潇洒摆谱,称得上当时的时髦。
董鼎山从密苏里大学毕业,就来纽约撞大运找工作。有了工作和基本保障后就想到生计问题,开始到纽约当年杜威和胡适创建的华美协进社去参加活动,希望多遇到些中国女孩。但在华美协进社的经历也打碎了董鼎山娶华人女孩的梦,他被吓到了。之所以被吓到是因当年的这些等着钓金龟婿的公主们眼光太高。她们大多养尊处优,颐指气使,而且要管辖男子,希望他们在家庭和事业上由她们来安排命运。董鼎山受不了这个。
与中国公主相比,那时来美留学的欧洲人就朴素且简单多了。于是,董鼎山就调整了方向。他发现,来美国读书的北欧女孩最朴实,能吃苦且善解人意。瑞典和挪威的女孩多来自小镇和乡村,她们身材高挑,气质天真贤惠。跟他交朋友时处处想着替他省钱;出门不愿坐当时堪称奢华的taxi而愿意步行,不吃豪华餐宴而选麦当劳。董鼎山娶了洋妻却享受了中国贤妻良母的待遇。
董鼎山妻子学会了做麻婆豆腐和红烧肉,跟他相濡以沫相爱了一辈子。我每次去他们家跟董先生访谈写作,她都备好茶点鲜花,然后躲开。后来熟稔了,她偶或轻声加入我们的谈话。凡熟识董鼎山者皆知她是一个现代难找的“古代”贤妻。
2015年5月,比他小八岁的妻子蓓琪去世。同年12月,93岁的董鼎山告别了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