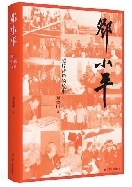
刘金田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2024年6月出版

中山植物园里的回忆
1985年2月3日,邓小平在韩培信、向守志、郭林祥、沈达人、顾秀莲等陪同下前往灵谷寺、中山陵、中山植物园和紫金山天文台参观。这张照片是在中山植物园参观时的情景。
离开中山陵,邓小平来到了中山植物园的温室参观。本来安排邓小平首先参观药物园。可是,邓小平在省负责人的陪同下,径直来到温室前。当他们走进温室时,主人却未到,邓小平一边等待,一边观赏千姿百态的盆景。不一会儿,研究所副所长杨志斌赶到了。
不知是太兴奋了,还是太紧张了,一时间杨志斌连客气话也不会说了,竟情不自禁地脱口说道:“小平同志,多亏你批了八个大字,我们才能够回到这里来!”
不知是邓小平没听清楚,还是话题太突然,邓小平似乎没有听懂。在一旁的江苏省省长顾秀莲对杨志斌说:“小平同志耳朵不太好,你声音说大点。”于是,杨志斌又大声重复了一遍。邓小平听懂了,他回忆了一下说:“对!是有这回事,一晃都过去十年啦!”
十年前的批示
事情发生在十年动乱期间。起因是1974年江苏省植物研究所全体科研人员和职工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反映他们研究所面临的困境。
南京中山植物园,其前身是1929年建立的“孙中山先生纪念植物园”。1954年,在“孙中山先生纪念植物园”旧址上重建了中国科学院南京中山植物园。到“文革”开始前,该园已建立起“苗圃试验区”“药用植物园”“材用树种园”“松柏园”“树木园”和“分类系统园”共700余亩,科研大楼拥有植物标本40余万份,还与40多个国家的300多个植物园建立过种子苗木交换关系,引进了油橄榄、速生松和优良绿肥等植物。
“文革”开始后,中山植物园的厄运接踵而来。全所人员被“下放锻炼”,研究所被并入其他单位。研究基地被不相干的单位占用,大批名贵树种被砍伐,苗圃与温室被辟为水稻田、菜园。1972年夏,《中国科学史》作者,八十高龄的李约瑟先生来到南京,指名要看看中山植物园。接待人员只好以“植物园人员外出斗、批、改”为托词而婉言谢绝。李约瑟说:“我研究中国科学史数十年,早就想亲眼看一看世界闻名的中山植物园。人员去斗、批、改了,植物不去斗、批、改,能不能让我去看看植物?”结果还是遭拒绝,他只好遗憾地离开南京。
植物研究所的领导、科研人员和职工多次向上级有关部门打报告,要求归还被占用的房屋和园地。可是,一个个报告如石沉大海。植物研究所从领导到员工由气愤变成了气馁,由失望变成了绝望。
1973年3月,邓小平恢复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植物研究所的干部凭着“直觉”,认定邓小平是值得信赖的,于是鼓起勇气,给邓小平写了一封5000余字的信,并在研究所发起了签名活动。1974 年6月中旬,这封寄托着植物研究所干部群众对邓小平无限信赖之情的信终于发出,并很快到了邓小平手中。邓小平看完信后很快写了批示:
军队占用地方房屋,凡能腾出的都应归还。此件转给南京军区处理(如来信属实,应坚决归还),并向军委报告。
邓小平作出批示的当天下午3时40分,国务院值班室即向江苏省委打电话,随后,南京军区也接到中央军委办公厅转来的邓小平的批示。这样,归还中山植物园的问题很快解决了。
当归还植物园的喜讯传来时,植物研究所的干部群众几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兴奋之余,植物研究所的负责人多方询问,得知是邓小平作了“如属确实,坚决归还”的八字批示。尽管他们并没有亲眼看到邓小平的批示,可他们坚信不疑地向群众传达说,多亏邓小平作了这八个字的批示,我们才能够这么顺当地重返植物园。
“我给你们签个名吧”
了解了这段历史,人们对杨志斌见到邓小平时所表现出来的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情也就可以理解了。所长贺善安向邓小平介绍了改革开放以来研究所为经济建设服务和加强国际科技合作等方面的情况。邓小平认真地听着,不住地点头。
在参观时,当邓小平看到一盆标名“峨嵋海棠”的植物时问道:“这真是峨嵋山的吗?”“这是在峨嵋山发现的,而且是在野外环境下偶然发生的一个自然变异,是海棠属科中很难得的珍品。”贺所长回答说。邓小平听了高兴地说:“哦,这是我们四川峨嵋山的东西。”这是一位普通老人多么真切的乡情。
中山植物园是以研究培育仙人掌类植物著称于世的。邓小平兴致盎然地观赏着。当他看到有株巨大的仙人掌一直长到房顶时,很感兴趣地问道:“再长高怎么办呢?”贺善安回答说:“为了不影响它生长,我们就把它锯掉一截子,让它缩回来再长。”邓小平听后说:“噢,这是个办法。”接着,他又风趣地说:“你们应该把房子接上一层嘛!”一句话,引得在场的同志全都笑了起来。
原定参观的时间已经到了。这时贺善安向邓小平提出了题词的要求,邓小平看了一下身边的工作人员,和蔼地对主人说:“这样吧,我就不题词了,我给你们签个名吧。”他在签名簿上写道:“邓小平二月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