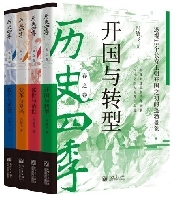
冯敏飞著 新世界出版社2024年4月出版
史上第一位“仁宗”
谥号是在死之后,后人依据地位高者生前表现,予以一种称号。这种称号分三类,即美、平、恶。美谥是褒,恶谥是贬,平谥是怜。恶谥如暴、昏、炀、厉等。美谥就多了,据统计占89.3%,最常见“文帝”“武帝”,再就是“孝”“英”“哲”等。“仁”也不少,如西夏仁宗李仁孝、明仁宗朱高炽、清仁宗爱新觉罗·颙琰(嘉庆帝)。北宋赵祯为史上第一位“仁宗”。
追加美谥的目的,无非奢望后任帝王“见贤思齐”。然而,美谥多属溢美之词,大都名不副实。不过,赵祯这“仁”倒是颇贴切。赵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有天加班到半夜,赵祯饿了,很想吃碗羊肉热汤,竟将口水咽了回去,第二天与皇后闲谈才说起。皇后怨道:“陛下日夜操劳,想吃随时吩咐御厨就是,怎能让龙体受饥?”赵祯说:“朕昨夜如果吃了羊肉汤,御厨就会夜夜宰杀,一年下来数百只,形成定例。为朕一碗饮食,创此恶例,于心不忍!”
对别人则相反,又宽又仁。如谏官王素劝赵祯不要亲近女色,赵祯说:“近日,王德用确有美女进献,朕确实喜欢。”王素坚持说:“臣今日进谏,正是怕陛下为女色所惑。”赵祯只好下令:“王德用送来的女子,每人各赠钱300贯,马上送出宫。”王素慌忙说:“不必如此匆忙!既然已经进宫,还是过一段时间再打发为妥。”赵祯笑道:“朕虽为帝王,与平民一样重情。我怕久了,会不忍心送走。”想想有“小太宗”之誉的唐宣宗李忱,他曾迷恋一位绝色佳丽,忽然担心重演老祖宗李隆基的悲剧。左右建议将她放出宫,他却说:“放回去我会想念她,不如赐一杯毒酒!”两相对比,天壤之别。
赵祯在位41年,为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其间,国际和平,国内和谐,政治、经济、文化都得以长足发展,GDP占当时世界的65%,特别是“和而不同”的士风成为一道亮丽的历史风景。
非“明君之仁”
对于赵祯,好评如潮。但在此,我更想“鸡蛋里挑骨头”。
有些人总觉得宋朝太弱,不如汉唐威风。我为其辩护,主要是大宋生不逢时,燕云十六州早被出卖,失去了长城屏障,更重要的是对手不再是匈奴那样的“流寇”,而是比汉唐时厉害得多的“半汉化国家”辽、夏、金及蒙古帝国。再说,宋之前面对的是匈奴、吐蕃,他们对中原政治或者土地并不感兴趣;宋及其之后面对的蒙古人、满族人不仅感兴趣还要完全吞并,两宋在这种历史性巨变的过渡时期,能长期与辽、金、夏并存并实现繁荣,已属不易。那么,赵祯是完人?当然不是!思想家王夫之指出:
计此三十年间,人才之黜陟,国政之兴革,一彼一此,不能以终岁。吏无适守,民无适从,天下之若惊若鹜,延颈举趾,不一其情者,不知其何似,而大概可思矣……夫天子之无定志也,既若此矣。
所言甚是。赵祯使命感挺强,很想主动解决盛世的“久安之弊”,要求范仲淹开列当务之急。范仲淹不失理智,认为“非朝夕可革”,所以“始未奉诏,每辞以事大不可忽致”。赵祯一再派人催促,朝野舆论压力增大,范仲淹才上呈改革方案,付诸实施。结果遭到旧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指责范仲淹等人搞“朋党”。赵祯吓了一跳,马上叫停改革,罢了范仲淹的官。
赵顼即宋神宗继位后,曾向王安石提出一个课题:“祖宗守天下,能百年无大变,粗致太平,以何道也?”王安石以《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为题作答,对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的统治做了总结,其中对仁宗着墨最多,但是于“无事”当中谈“有事”,褒中含贬,笔锋一转:“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无亲友群臣之议”,小心翼翼暗示“祖宗不足法”,明确地强调“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鼓动大胆改革。近代历史学家蔡东藩直言不讳地指出:
仁宗之驾驭中外,未尝不明,而失之于柔……仁宗以仁称,吾谓乃妇人之仁,非明主之仁。
范仲淹的改革内容有10项,其中5项属于吏治,两项与吏治有关,总计70%涉及政治体制。他派一批官员深入各地去现场考核,自己坐镇中央指挥,将各地报来不称职的名字一个个勾掉撤职。枢密副使富弼在旁看不过意,提醒说:“您一笔勾了很容易,但这一笔下去要让他一家人哭啊!”范仲淹回答:“一家人哭总比一路人哭要好吧!”当时的“路”相当于现在的“省”,范仲淹想的是大局。
作为明主,就应当为了一国人不哭,而不惜让某一家几家人哭。那些官员,平时跟着范仲淹大唱“先天下之忧而忧”的高调,一到改革,哪怕影响点“灰色收入”就受不了。如此,赵祯却一味地“仁”,不惜迁就那少数人,叫停改革,让弊政继续积累,从而让朝政危机由轻到重,显然不是“明主之仁”,而只是“妇人之仁”。
赵祯“妇人之仁”所受益之人,恐怕有限。著名大臣包拯认为当时纳税户口“有常数”,土地产出“虚耗”,财政收入却增长一倍有余,表明“诛剥贫民”“重率暴敛”正愈演愈烈。他责问仁宗:如此“日甚一日,何穷之有……”,国家根本如何安固?
包拯说了也白说。此后十余年,刘挚上任冀州南宫县令时发现,该县“民多破产”,原因正是民众实际负税无形中翻了一倍有余。他要求按市场价折算绢绵,结果却招致“转运使怒,将劾之”,只因偶遇包拯才保住那顶乌纱帽。差不多同时,状元出身的大臣郑獬也进谏,反映他家乡安州“类多贫苦”,“虽岁丰谷多,亦不敢收蓄,随而破散,惟恐其生计之充,以避差役”。简直可以说衙前之役猛于虎。然而,赵祯却不敢改革这些苛政。
一个帝王如果不能把握好国家发展时机,而留下诸多隐患,尽管显赫一时,也不能算是真正优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