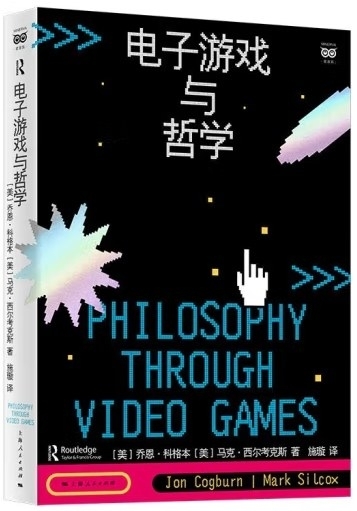
《电子游戏与哲学》 [美]乔恩·科格本 [美]马克·西尔考克斯著 施璇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4年9月出版
本书从对当下各种广泛流行的电子游戏的反思中,谈论几个具体的哲学问题,比如外部世界的问题、个人同一性问题、人工智能的本质、道德与暴力的关系、人生的意义等等,它巧妙地把游戏体验与哲学思考融合在一起。
为何我们会认为一个人可以通过电子游戏这一媒介获得哲学的智慧呢?一旦某人在游戏设定的高度具体的任务上经历成功(或失败),当心灵抓住残留的思想,哲学家的工作就此开始。
无论人们刚刚玩过像《吃豆人》这样的简单游戏,还是像《生化奇兵》这样深刻且令人沉浸的艺术作品,游戏老玩家们最终总是会发现自己在思考刚刚所在的游戏叙事世界中某些生动的意象、某些古怪的游戏玩法或是某些异常的特征。这些想法一闪而逝。但对于有哲学倾向的人来说,它们也可能会导致深深的困惑、睡眠不足、职业的转变或者皈依。
尽管很少有玩家意识到当他们进行这类反思时,他们正在参与一项贯穿整个西方文化史的古老实践。哲学的系统的、自觉的实践实际上源于早期的历史追求,比起抽象推理来说,这些追求更加接近于玩游戏。
也许最著名的关于游戏的现代哲学论证是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对“图钉游戏与诗歌一样好”这一观点的批评。密尔是一个享乐主义者——他认为世界上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东西就是快乐。
但密尔被其他有享乐主义倾向的哲学家(尤其是他的先行者杰里米·边沁)所赞同的观点吓坏了,这个观点主张像图钉游戏这样的简单游戏与伟大艺术作品之间的价值差别只能通过它们在现实世界中所提供最大快乐的人数来确定。如果更多的人从玩《骑士比武》中获得乐趣,而非从看马奈画作中获得乐趣,那么按照边沁的标准,这就让《骑士比武》在客观上更有价值。
为了反对这一观点,密尔认为有必要在他所称的“低级”快乐与“高级”快乐之间作出区分。他认为,后一类快乐应该具有更多的真正的价值,即便很少有人能够享受它们,因为它们会被密尔称为“有能力的法官们”所选择——所谓“有能力的法官们”是指经验丰富且能够进行广泛比较的人。
然而,过去二十年左右在哲学中一种密尔式关切涌现出来。以《哲学走进电影》《葡萄酒哲学》《情色哲学》《恐怖哲学》为名的书籍已经大量上架,出人意料地引来了大批热情的读者。并非所有这些书籍的作者都认同哲学上的享乐主义。但他们似乎都相信理解我们如何玩得开心并且对如下一些问题提供实质性理由都是哲学的工作,例如,为什么最老的法国勃艮第红酒比最新的澳大利亚西拉红酒更好,或者为什么《魔鬼的诅咒》比《13号星期五》更加值得一看。
我们从年轻时培养出来的对电子游戏的哲学之爱,至今依旧丰富着我们的生活,正是这份爱让我们希望自己可以在这个广受欢迎,但仍然分析不足的新媒体中,为一些最伟大的艺术作品提供类似的服务。我们见证了电子游戏作为一种娱乐形式以及一种(最终的)艺术形式的发展,与此同时发展的还有我们对哲学所产生的浓厚兴趣。
当然,电子游戏中有很多让哲学家感兴趣的东西,不论他或她是否认为一些游戏是真有价值的艺术作品。它们作为新颖的娱乐媒介以及人们制作即便是最简单(最丑陋)的游戏时在逻辑上和心理上所付出的大量努力,这些现象本身无疑就值得严肃的哲学关注。
另外,我们还希望表明许多电子游戏的吸引力更加接近于伟大的诗歌,而非一目了然、玩过就忘的图钉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