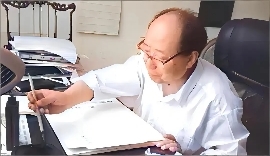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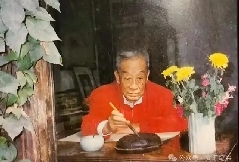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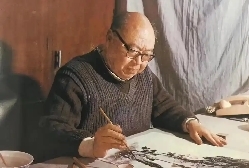
在朱桂老家吃过的饭
做过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并代国务总理的朱桂莘(启钤)先生,家中厨艺极讲究。那时朱桂老已搬到东四八条,桂老的哲嗣朱海北先生与我的祖母同在政协学习,我家又住在东四二条,相隔不远,往来颇多。朱海北的夫人亦善烹饪,常有饮食相贻,只是我彼时太小,吃过他家什么东西,已经记不清了。
以前开会时偶然与王畅安(世襄)先生、罗哲文先生同席,席间说起朱桂老家菜做得如何好。畅安先生与罗哲文先生又恰在朱桂老办的“营造学社”供职,于是我就问二位是否在朱家吃过饭。两位先生都说吃过,罗先生对饮食不太在意,记不清吃过些什么,只说菜是极好的。畅安先生是美馔方家,能列举出朱家好几样拿手菜来,特别举出朱家的一味“炒蚕豆”,印象颇深。是用春季的蚕豆,去掉内外两层皮,仅留最里面的豆瓣,和以大葱清炒,不加酱油,仅用少许盐、糖清炒,味道独到。
“取法乎上”的文物专家
早前北京有两本书颇为畅销,一是朱季黄(家溍,见左图)先生的《故宫退食录》,一是王畅安先生的《锦灰堆》。这两本书先后出版,有异曲同工之妙。季黄老与畅安老是总角之交,两人相差不到一岁。从祖籍来说,一位是浙江萧山,一位是福建闽侯,但都是生长在北京的。季老与畅老同是文物专家,又都是上一辈的文化人。
说到吃,季老自称是“馋人”,但在饮食方面并不讲究。有一年我曾请季老在家中吃饭,备了几个家中的拿手菜。如蟹粉狮子头、清炒鳝糊、淮扬虾饼等,季老吃得十分高兴。
畅老比季老技高一筹,不但好吃,且能亲自烹制。他做的面包虾托、清煨芦笋、虾子茭白等颇负盛名。有次我问畅老北京何处有卖虾子的,畅老立即告诉我现在很难买到,仅红桥农贸市场地下一层有售。可见在原料方面,畅老也是事必躬亲的。
季老在《故宫退食录》中有“饮食杂说”二文,说的大多是他吃过和见过的东西,绝对没有什么“饮食文化”之类的探讨,实实在在。说到朱家做黄焖鱼翅的方法是向谭篆青(祖任)家学来的,真可谓是正宗正派。就像季老学武生问业于杨小楼及他的传人与合作者刘宗杨、钱宝森、王福山等,可谓“取法乎上”了。
“溥八爷”擅制辣酱油
画家爱新觉罗·溥佐(见中图)先生号庸斋,与雪斋溥伒先生是堂兄弟,大排行八,人称“溥八爷”。溥佐先生与我家有远亲,五六十年代常在鄙宅,后来他调到天津美院任教,往来才少了。这位溥佐先生早年以画马著称,后来山水、花卉、翎毛均很擅长,晚年成就斐然。他是觉罗宗室,好吃自不待言,只是中年景况欠佳,好吃而不能常得,因此常在我家吃饭。
他有一样“绝活”,就是自制辣酱油。这辣酱油本不是中国调料,实属舶来品,在西餐中是蘸炸或煎制肉食的,有点类似广东的喼汁。过去以上海梅林公司所制的黄牌或蓝牌辣酱油为最佳,凡高档些的菜市场中都有卖的,谁也不会去自制。唯独这位“溥八爷”擅制辣酱油,方法秘不示人。他曾送给我家辣酱油,是用普通酱油瓶装的。打开香气扑鼻,吃起来远胜过梅林公司所制,浓黑醇厚,如用之蘸炸猪排,鲜美无比。问“溥八爷”制法,他只是笑笑,说以丁香、豆蔻等为基本原料,要经过七八道工序,往下就不说了。
邓家的菜经历了三个等级
上海的邓云骧(云乡,见右图)先生与我是忘年之交。记得第一次去上海拜访邓先生家恰逢端午节,那时邓先生的夫人尚健在。农历五月初的上海已经很热,从我住的静安寺到邓先生住的杨浦区要一个多小时的路程。溽热难当,坐定后邓夫人端来两个粽子。不过是普通的糯米粽,粽叶却是碧绿的,发出一股清香,不像北方的粽子大多是用宽苇叶包的。那粽子是冰镇过的,剥开粽叶后又浇上紫红色的玫瑰卤汁,色泽晶莹可爱。我在北京吃小枣粽或豆沙粽都要蘸些糖,从没有蘸玫瑰卤吃过,味道确是不同。请教邓先生玫瑰卤的调制,他说是夫人调制的,他也不得其法,却是用鲜玫瑰花做的。邓先生对“红学”研究颇深,这玫瑰卤或得益于《红楼梦》,亦未可知。
云骧先生曾写过他家擅做杭菜,如金银蹄、炸响铃、八宝鸭子之类。其夫人蔡时言女士是浙江人,杭菜自然做得很好。20世纪90年代初,邓夫人已经过世,家中是请一位保姆烧菜。据云骧先生讲,他家的菜经历了三个等级。最好时是由邓先生的大姨子,即蔡时言女士的胞姐来烧,那是最好的,他在家中宴请谢国桢、俞平伯、许宝骙诸先生时都是由大姨子来烧的。大姨子过世后是由邓夫人自己来烧,是第二等级。邓夫人烧的菜我是吃过的。邓夫人过世后则由保姆来烧,凡请客时均由邓先生亲自指导。
在陈从周先生家吃常州饼
中国著名古建筑园林艺术学家陈从周先生生性耿直,敢于直抒己见,为此得罪了不少人,但他待人却非常热情宽厚。80年代我去上海,到同济大学宿舍拜访先生。正值他午睡方醒,兴致很好,从我的伯曾祖次珊公一直说到蒋百里(方震)先生的经历,两个多小时毫无倦意,又乘兴为我画了一幅竹子,题为“新篁得意万竿青”。我看已近黄昏,起身告辞,陈先生执意挽留,并对我说,当晚家中吃常州饼,且晚饭后华文漪、岳美缇要来一起唱昆曲,要我一定不要走。盛情难却,只得留下来。晚饭其实十分简单,只有常州饼和稀饭。那常州饼做得极好,直径有五寸许,类似北方的馅饼,以油菜为馅。南方的油菜比北方的鲜嫩、好吃。饼的皮子绝对不像馅饼那样硬而厚,简直可说是薄如宣纸,油菜碧绿的颜色映透皮子,晶莹可爱。用筷子夹起,虽绵软异常而不糟,吃到嘴里还有些韧性。
陈先生告诉我常州饼的做法关键是和面,不似北方馅饼是揉出来的,而是用稀面调出来的。方法是干面兑水后用筷子顺时针方向不停地搅,先稀如浆,逐渐加面粉,直到搅拌不动即可。用时稍用干面以不黏手为度,包上馅后即放铛上,因此皮子才能如此绵软而有韧性。春天的油菜清香碧绿,透过皮子若隐若现,不但口感好,观感亦极佳。先生有文集二,一曰《春苔集》,一曰《帘青集》,取“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之意,先生在饮食上的恬淡与清雅或与园林艺术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
其实,以上谈到的许多先生前辈都不以名人自居,也绝不说自己是美食家,更不谈什么“饮食文化”。这些老先生们对生活的平实追求与热爱,非常纯真,远不是某些浮躁“名人”标榜的什么“饮食文化”。
(摘自《个中味道》,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