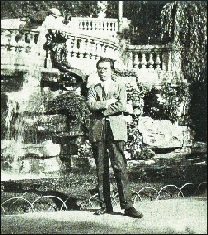
刘海粟在欧洲考察写生

刘海粟等人在德国办展览
蔡元培先生影响他一生
父亲作为美术教育家与美术史论家,有着东西方艺术开阔的视野,无论是中国画、油画还是书法,他的创作中凸显着中国文化中苍莽浑厚、刚劲雄强的一面。
1912年,年仅17岁的父亲在上海虹口区乍浦路上一幢普通的石库门房内,与乌始光等一起创办了上海图画美术院(即后来的上海美专)。开放的理念、创新的魄力、挑战的勇气,因办校,父亲受到了北京大学校长,后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的赏识和鼓励。
1922年蔡元培先生出任上海美专校董会主席,提出了“闳约深美”的治学及办校方针。父亲立刻撰文表达了自己对这四字箴言的理解,就是要以“不息的变动”作为美专自身的精神内核。他不仅将这四个字作为办校方针,也将它作为了自己从艺的理念,求新求变,一生追求时代精神,时时刻刻都敢为人先。
1929年,父亲受教育部之命赴欧洲游学考察。蔡元培先生不仅为父亲争取到了赴欧洲考察名额,还聘任其为大学院的挂名撰述员;之后,他全力支持了父亲举办“中国现代展览会”的计划,令这一中西文化艺术交流史上的壮举,成为了当时欧洲艺坛最大的盛观。
父亲晚年一直和我们回忆第一次去欧洲前,蔡先生对他说的一席话:此行不是为了你我个人,希望你们学成归来,为国服务。蔡先生的这段嘱咐,父亲始终谨记。
1952年秋,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上海美专与苏州美专、山东大学艺术系的美术和音乐两科合并为华东艺术专科学校,简称“华东艺专”。在学校赠送的纪念册扉页上,父亲充满激情地写了这样一段话:艰苦缔造的美专,为了中国的新兴艺术战斗了40年,现告一段落,调整为华东艺专。伟大的精神和灿烂的战绩,将永远留在中国人民的记忆里……一切的一切都贡献给祖国。
1934年,排除了各种困难,“中国现代展览会”在德国召开。在开幕式发言中,父亲用这么一段话来总结中国艺术:“中国画学之特质,不用如法律般要求着辩护人,也不要向科学般去证明,更用不着批评与分析,我们只须让图画去感应与说述……这次展览各画,对于任何德人得能亲近认识与了解中国特质,而具有普遍与时间无限性的美。”
结合父亲一直对我说的,学画不单是学画,更要紧的是了解中华传统文化,我认为,虽然艺术史都将“融汇中西”作为父亲的艺术特点,但父亲不论在理念还是创作中,都忠实于自己血脉中的传统因子。
父亲的精神气一直很足
我是父亲最小的女儿,出生时,父亲已50多岁了。有很长一段日子,我都陪伴在他身边。父亲的精神气一直很足,他喜欢书写催人奋进的内容,如“精神万古,气节千载”,这可以说是他的座右铭。他多次对我们讲,“精神万古”就是一切艺术都是精神的创造,从事艺术的人,都应追求这种万古不朽的精神。“气节千载”讲的是一个人的品格。从事艺术的人,尤其要讲这种气节,要有凛然与浩然之气。
父亲晚年三次中风,更不用说那场旷日持久的磨难对他精神的折磨,但他以超越常人的坚韧意志藐视一切,以旺盛的生命力和高度的自信战胜了一切砥砺。困难的时期,我亲眼看着母亲与父亲一起,克服了各种令人难以承受的压力,镇定自若地处理日常的生活;而且他们都是非常乐观的,从没看到他们唉声叹气或愁眉苦脸。
人处逆境,最难的是能控制自己的情绪。父亲说,只要想到司马迁忍辱成书,想到曹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再自问光明磊落,问心无愧,便能心平气和地在地板上睡觉、在搁板上创作。全家蜗居在弄堂里的那些日子,父亲依然想方设法弄到了纸笔。
有一次,父亲的学生陈钧德的妻子罗兆莲送来了一盏旧货市场淘来的台灯,父亲高兴极了,因为对于画家来说,光线实在太重要了。他因此画得更起劲了。后来,他曾在给新加坡收藏家周颖南的信中,倾诉自己的人生感悟:“不息劳动创造,能够使你伟大,而享受到真正幸福。”
1977年,父亲开始用“年方八二”来题字落款,他称这是仿照旧时戏曲小说年轻女子“年方二八”的称呼,表示自己依然有青春之心。更重要的是,他希望“今后的新创作是一连串的杰作”,将超过自身65年来的所有作品。
1988年,父亲决定第十次上黄山时,已是93岁高龄。收到他的信,我立刻赶去南京陪他。一早,安徽省政协派车送我们,南京到黄山,车程可谓遥远。中午在宣城歇脚,大家都劝他慢慢来,他却执意吃了饭就要继续赶路,说“等不了,我要去画黄山”。于是我们当天就赶到了黄山,住在山脚下。第二天一起身,他便开始写生,学生劝他,“海老,不要太累”,他答,我要怕苦怕累就不出门了。画完后又催着我们要立刻上山。可以说,他对黄山的每一棵松树、每一块奇石都了然于胸,但每次上黄山,他都充满创作的激情,像第一次登山一样,抱着极大的热情,去寻找新的绘画灵感。
父亲给艺术界留下的,远不止书画图卷,更是一种精神激励。他曾说:“我的黄山画中有许多自己的影子,具体而言一是豁达、豪迈的品格契合,二是天真烂漫的情怀寄托,三是不息变动和创新精神的应和。”父亲确实以漫长而充盈的一生,实践了“闳约深美”。
(摘自1月3日《新民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