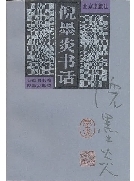
(摘自《倪墨炎书话》,北京出版社出版)
招贴栏上的小条
这是1976年的事。这年春天,我被借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参加《鲁迅全集》的编辑注释工作。那时我家住在上海愚园路。一天,我在胶州路口的招贴栏上,在交换房屋、对调工作、修理家用电器、出让木器家具等等的招贴中,发现一张用苍劲的钢笔字写成的小条:
出让全套《文艺报》。价格面议。接洽地址:愚园路某某弄某某号沈。
我把地址抄了下来。
第二天是星期日,上午八时,我就根据所抄地址找上门去了。我揿了电铃,一个小伙子来开门,待我说明来意,他就转向里面喊道:“爸爸,又有人来买你的文艺报了!”接着,一位70多岁的清癯的老叟出来,连声说:“真抱歉,真抱歉,文艺报昨天下午已有人买去了。”我立刻通报了我所在单位,我的姓名,并向他说明:我爱好现代文学,正在用心收藏“五四”以来的旧书旧期刊。他好像略知我的姓名,对我打量了一下,扬手让道:“那就请里面坐吧!”
这是一间明亮、整洁的书房兼卧室。他让我在小圆桌旁坐下,自己坐在对面,说:“我看过你写的文章。早就猜测你大概在出版社服务的。解放前我也是搞这一行的。”我喜出望外地询问他在哪家出版社工作过?他不回答我的问题,却说:“我编过杂志,也编过书。”我向他请教20年代、30年代文学界和出版界的一些事情。他兴致来了,从北京文坛谈到上海文坛……从他的谈话中,我知道了20年代他在北京工作,以后定居上海,解放后改行在中学教书,60年代初退休。
“今天就让你看看我的破书吧!”
我心想:他那么熟悉文艺界和出版界的情况,一定有不少藏书吧?他大概看出了我的神情,谈话戛然而止,站起来说:“今天就让你看看我的破书吧!”说着,他在西壁上一拉,像变魔术似的,哗的一声,打开了壁橱的门,里面整整齐齐装满了书,还飘出来樟脑的馨香。这时我才发现,东西两壁全是上顶天花板、下踏水泥地的壁橱。东边三橱,西边三橱,每橱分上中下三层。
我探头看了他随便打开的那一层,共三格,每格是两排书。这里是《论语丛书》《人间世丛书》,林语堂的集子,邵洵美的集子;虞琰的诗集《湖风》,我还是第一次看到,鲁迅在《登龙术拾遗》中曾不指名地提到过她;曾今可、张若谷、傅彦长、邵冠华等人的集子,都是我所不藏的;最下面的一格,竟还发现叶灵凤的几种集子。
“你把叶灵凤归在论语派?”
“我随便打开的这一层,最乱,放的是论语派和不好归类的一些人。叶灵凤可以把他放到创造社那一橱去,也可把他列入现代派,但后来和傅彦长等人也接近过。”
我关上了开着的橱门,转向东边第一橱。啊!这里简直是一个宝库。我爬上小木梯,从第一层看起。这里是我国新文学的第一批著作:全套的晨报丛书、新潮丛书和新潮文艺丛书,十分难得的清华文学社丛书,大量的北新书局的书,鲁迅著作的初版本毛边书,刘半农的著译;钱玄同的几种大开本的音韵学和语言学的书,也收集齐全了。周作人的书放了整整一格。我忽然想起,他这么多“反动派”的书,“汉奸”的书,文化大革命初期“横扫一切”“大破四旧”的时候,是怎么在劫而脱逃的呢?
沈老先生淡淡一笑说:“我是退休教师,冲击自然少些。更重要的,红卫兵‘扫四旧’前,我已有了准备。我买了墙纸,把两边壁橱糊住,每边再贴上毛主席不同时期照像八幅。红卫兵即使知道这两边是壁橱,他们也不敢撕毁伟大领袖的像啊!”
“那后来怎么又把墙纸撕了呢?”
“这样整整糊了九年,我可憋得慌啊!我多么想看看这些书啊!多么想摸摸这些书啊!今年2月,我一位同事平反,抄去的书也还给他了。我就在一个夜里把墙纸撕去。我抱着大把的书睡了一夜。现在大家都不想再乱来了。你不是去参加《鲁迅全集》的注释了吗?我们都希望我国的文化复苏啊!”
“要让给和我一样爱书如命的人”
我一边在小木梯上往下爬,一边说:“老伯的子女可也有爱好藏书的?”
他让我仍在小圆桌边坐下,自己也坐到对面的藤椅上,叹口气说:“我有三个儿女。我一生积储起来的这些破书,他们没有一个喜欢的。”“那么,日后您送给哪家单位?”
“不敢夸口,我的破书中,相当一部分,就是北京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也是缺藏的。当年要是给唐弢、钱杏邨知道了,他们还不天天在我屋前屋后转!……我这些破书,要让给和我一样爱书如命的人。老弟有意,当然也是人选之一。”
我的心房剧跳起来:“老伯要是肯把全部藏书让给我,真不知要怎样厚答您老才好!我个人财力有限,但我有几位爱书的好友,如《人民日报》编副刊的姜德明、钱杏邨的女婿吴泰昌……”
“现在我可不能出让!”他的眼神变得忧郁起来,“这些书伴了我大半辈子,我怎么忍心把它们搬走。没有了这些书,我每天做些什么呢!必须等我行将就木之时……”
这时进来一位五十开外的妇女,说:“已快一点钟了,真该吃饭了。老二肚子饿得厉害,已在厨房里吃过了。这位客人也在这里用餐吧。”我站起来礼貌地喊道:“伯母。”
“我内人过世已快20年了。她是刘妈。”沈老先生说。我赶紧向沈老先生告别,临走留下了地址。
“那老先生的书呢?”
1979年4月间的一天,和我同室办公的胡启明偶尔与我谈起,约2月前的一个星期天,他在静安寺新华书店闲逛,一个青年问他:你要不要旧书旧刊?
我猛然想起沈老先生。这天下午我请假匆匆去看望沈老先生。大门虚掩着,敲了几次,无人回音。推开老先生的书房,烟雾迷漫,四个人正在打麻将,两壁壁橱已拆除,露出白墙壁。“你找谁?”“沈老先生。”“我父亲三个月前已过世。八索我吃!”“那老先生的书呢?”
“你大概就是和我父亲谈好要买他书的那位倪先生吧?”
“是的,是的。”
“我父亲病危后,天天念着要找你。你留下的地址,和煤气票、自来水票一起压在小圆桌玻璃板下,不知什么时候丢了。二筒,我和啦!”我看清楚了,说话的人30多岁,颜容苍老,他就是沈老先生的大儿子吧。
“那老先生的书呢?”
“父亲死后,我家老二,星期天特地上书店找过你,以为你喜欢书,总常常跑书店的。东风,拍!南风!”另一副牌已砌起,他一边聚精会神地打牌,一边说,“后来实在找不到你,书就卖给了旧书店!”
我离开了沈家,沉重地走在愚园路上。走了约100米,刘妈拿着个纸包追了上来。她眼角上有了颗水珠,说:“老先生一死,他们要我走了。那些书共卖了500元,送给我300元,说是留个纪念!”
“全部书只卖了500元!”我惊讶地说。“旧书店的人说,要在两年前,他们再贱也不要。还说是反派角色的书多,不知有不有单位要呐!”我深深地叹了口气。这时她把纸包递给我,里面是10本书。她说:“旧书店那天来搬书,我趁他们不注意时,就抽出了10本,给你留着做个纪念。”
我从她微微颤抖的手中接过10本书,五本是良友图书公司的硬面精装本:梁得所作《未完集》、倪贻德作《画人行脚》、鲛人作《三百八十个》、大华烈士译《十七岁》、赵家璧译《今日欧美小说之动向》。这五本书不是一套丛书里的,但开本、装帧相仿;三本是现代书局出版硬面精装本:《田汉散文集》、叶灵凤作《未完的忏悔录》、杜衡作《叛徒》,这三本书也不是一套丛书里的,但开本装帧也相仿;两本是商务印书馆的硬面精装本《文学研究会创作丛书》:杨骚著《记忆之都》、李广田著《画廊集》。这10本书都像新书一样,有护封的两本,护封也是新的。我从袋里摸出二张10元钞送给她,说:“我没有别的东西送你,请你收下。”她却生气了,用力推了回来,说:“我若要钱,就不留下这些书了。这是老先生给你留作纪念的。”
经过千方百计地向旧书店打听,后来才知道了沈老先生的一大卡车旧书的下落:一小部分旧书店留下作为自用的资料;一小部分存在旧书店仓库里,而一半已卖给了北方某油田的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