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叔瞅着包裹愣神。日子咋这么快?一场大冻,一场大雪,又一年。他掐着指头数一二三,倒没数了。向外张望,院子里除了风除了雪,没什么生气。就一些人家门口上挂着的大红灯笼,还透点喜庆的味道。收回目光,年叔一屁股跌在椅子上。椅子咯吱一声,提醒人——过年了。
屋外有人敲门。谁呀?我。
年叔听出来了,是关婶,赶紧把包裹藏进炕琴。折回身开门,见关婶拎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面团和肉馅。香香拎着一棵酸菜。
一阵风灌进来,雪花在门口飞舞。年叔把娘俩让进屋,搓着手说:“大过年的,你俩咋来啦?”拉亮电灯,又去捅炉灶。关婶看着壁柜上年叔老婆的遗像,气道:“这年让你过的。”
年叔脸红起来,要收起相框。关婶拦住说:“让嫂子瞅着,不好吗?”年叔一时无措,嘿嘿两声不言语了。
香香圆场:“年叔,俩好嘎一好,一起过个年呗。”
年叔用巴掌有意无意遮大腿。棉裤那儿漏个洞。关婶边洗手边笑:“别捂着啦,一会儿俺给你缝上。”年叔心思被看穿,低头给锅添水去了。
关婶说:“俺俩不来,你还不吃饺子了?”年叔傻笑:“石头不在家,俺光棍一条,哪来心情包饺子?”
关婶让香香剁酸菜,自己和面,念叨说:“石头刚从部队专业,就去驻村了,当书记能不忙吗?”
香香说:“石头哥一直跟俺联系呢,干劲儿老足了。”关婶说:“帮大家把日子过好,石头有道道,咱甭惦记了。”
年叔嗯了一声,说:“通讯方便了,人却更远了。倒不如在部队前儿,写信还能留个念想。”香香说:“石头哥脱了军装,也是穿军装的人。”
屋里有了人气儿,空气里就有了热乎劲儿。香香剁完酸菜,用纱布把菜馅包住,挤出菜汤,再把菜馅和肉馅搅拌在一起,香气立即弥漫开来。
关婶揉好面团,放那饧着,说年叔:“进里屋把棉裤脱了。”年叔支吾着:“合适吗?”关婶拉下脸:“漏着合适?”
年叔不得已进里屋把棉裤换了。
关婶穿针引线,说:“现在日子好过,干吗还这么苦着自己?”年叔有点不是心思,瞅着香香说:“这不想攒钱给石头娶媳妇嘛。”香香脸一红,跟着暗了。关婶连忙说:“算了算了,不唠这些,包饺子吧。”年叔说:“好啊,俺出趟外头。”
年叔裹上棉袄出门。屋外白茫茫一片,分不清天和地,不少孩子在玩耍。有了花灯,有了鞭炮声,空气里有些年味了。年叔揉揉眼睛,想抹掉点啥,却越抹越多。他生自己气了,在脸上堆起个好看,板着好看就进屋了。
三个人很快包完了饺子。年叔盯着饺子,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昂,在盖帘上列着队,兵似的。好看就有点不好看了。
关婶瞪过来一眼:“瞧你蔫了吧唧的性格,不能改改?不就孩子没回家过年吗?俺娘俩来陪你,看你脸子来啦?”
年叔笑出一脸腼腆。
年叔好久没吃上这么香的饺子了,想跟关婶说点感谢的话,却又不知从何说起,于是就闷头吃。关婶笑他“一吃一个不吱声”。
吃完饭,香香收拾桌子,关婶收拾年叔。“别胡思乱想了。香香爹去世早,俺娘俩不也得过?咱活出个样儿,才能给那头宽心。”
年叔连连点头。关婶又聊一会儿,看香香收拾完,该走了。
年叔问:“明儿初一,还来不?”香香抢话说:“来,年叔,明儿起早就来,初一照过。”年叔咧嘴就笑了。关婶气得也笑:“傻老爷们儿一个!”
年叔送娘俩出门,看风紧,回屋拿来一件军大衣给关婶。关婶问:“嘎嘎新,哪来的?”年叔说:“石头的,托人捎回来的,俺一次都没穿过。”关婶问:“真没穿过?”年叔说:“扒瞎干啥?”关婶把军大衣给香香披上,说:“要穿也该香香穿。”香香瞅眼年叔,挤出个笑意,接着就别了头。香香搀着关婶往外走,看娘眼里润润的,小声嘱咐:“别回头。”
年叔待在门口,望着关婶娘俩远去。风雪中,两个人影慢慢化成一个人影。眼前就有点模糊,感觉人影转了身,朝自己这头走来。走着走着,他看清了——是石头!
石头来到年叔面前,身姿挺拔,啪地来个立正,大叫一声“爹!”眼角余光却在寻香香。
年叔清清楚楚看到,儿子穿着军装,套一件雨衣,像刚从水里给捞出来。
年叔张开双手,没等拥抱,爆竹声大作,村里放烟花了。年叔使劲儿眨眼,哪有什么人影?只有繁花满天。年叔一时陷入恍惚,望着满天炫彩,耳边响起祝福声声。
年叔默默回到屋里,捧起老婆遗像,来到炕琴前。他打开柜门,解开头前儿藏起来的包裹。儿子的笑容迎出来。黑白的。
相框对着相框,黑白对着黑白。年叔冲老婆说:“石头在洪水里救出很多村民,死得光荣,咱该高兴才是。”
窗外,风停雪住,年味正浓。爆竹声更紧,烟花更绚烂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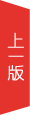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