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雨水是一种让记忆发胀变柔软的催化剂,它总让我想起那些已离开我生命的人和事物,想起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必须承认的是,有些人是台风,他裹挟巨风和暴雨,在你的生命中掀起惊涛骇浪,过往之地寸草不生,可你仍站立在风暴的中心,为迎接他倾洒的一抹暖阳而拼尽性命。多年以后,你仍记得那种暖,记得那巨大的激情,它在你周身的骨骼里猎猎作响,仿佛经火一点,仍旧会燃烧。有人是永远绵长的薄薄细雨,是日子,是光阴,是春天的河水和夜里的呼吸,你甚至听不见他到来和离去的声音,可他已在你生命里留下河流般广阔的印记。
关于雨水的记忆斑驳庞杂,那些画面在雨中浮现,也在雨中消散。
两年前在广州南沙的一个夜晚,下了班,在街边一爿小店吃晚饭。因贪读握在手里的一本书,心思沉浸在故事中,耳朵全然未听见小铺外面大雨从天空之上瓢泼而下的声音。等合上书出了店门,才发现外面的街道早已被淹没成大河。来来去去的车辆打着朦朦彩灯,仿若驾船似的漂浮在街道上。雨已停了,雨河尚在。我像个孩子,蹚在那街道和雨水做成的宽阔无边的大河之上,一步步往住的地方走去。那时,在那座小镇上,除了工作和日复一日的生活,我没有朋友,没有家人,没有人与我聊文学和艺术,我一心想着离开。可那天晚上在街上玩水过河的我,又是那么快乐。我想起儿时故乡的院子,因大雨而涨满了水的院子。祖母和姐姐坐在窑洞门口看电视,我在黑漆漆的院里拿着一张木板,拼命想要在涨水的河上划起船来。时至今日,闭上双眼仍能清晰记得那画面。短裤和粉红色罩衫都湿透,甚至额前的碎发也滴起水来。可我仍盲目折腾着,相信在黄土高原的一方小院里能划起船桨。我听见祖母朗阔的叫骂声,而后她把那个全身湿透的小女孩紧紧搂进她怀里。我的额头抵着她的下颌,颤抖着,战栗着,依旧不死心,想要去再试一把。下一次,我一定可以让木板在水上驮着我漂起来的。
长大后,来到南方,见到真正的江河与大海,见到漂游江上的洁白船只,才明白那个孩子的执拗与天真。今日我已完全长成一个成熟的大人,可我发现自己仍旧在以另外一种方式驾着一艘空无的船漂流在一个又一个异乡,打捞一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日复一日为它们付出时间和梦想。
二
夏天的时候,突发奇想在山城买了房子,凭窗可观渺渺江水。一直等到深秋将尽,才忽而想起,问自己为何匆促地做下这样的决定。这些年,总是漂泊在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地方,搬家,收拾行李,一次又一次离开。或许是感觉到乏累了,想停留,是这样的潜意识驾驭情感做出选择。情感是懒惰的、懦弱的,它需要安全感,总是拼命寻找依托,要么依靠一个人,要么依靠一方水土,哪怕是一座空荡荡的房子。既然时间留不住,这样的空间也许能给我一点安慰。
后来,当冬天渐渐来临的时候,忽而明白这样的做法是徒劳无意义的。一座房子只能留住肉身,它无法留住永远无处安放的灵魂。我深刻地明白着,这些年,自己一直是故乡的异乡人,也是居住在这座城市的异乡人,是身旁恋人的异乡人,是我自己的异乡人。同时深爱,同时背叛。同时靠近,同时逃离。这是被光阴层层烙印的事实,它犹如一枚印章,深深镌刻在一个人的骨子里。这场永无止境的雨水,是一张由孤独编织而成的网,终其一生,我都是流浪其中的囚徒。
前段日子一直被失眠所困,索性写了个关于失眠的小说。一个彻夜失眠的人,每到深夜总感觉自己的脑袋里有车辆驶过,翻来覆去睡不着,后来他终于找到一种可以入眠的方式。他在城市的夜晚游荡,发现了一种专门在夜间行驶的公共汽车,坐着这辆公车穿过整座城市的时候,他发觉自己终于可以沉沉入睡。后来每天晚上,他便乘这辆公车在整个城市的夜晚游荡,和这辆车上许多的失眠者一样。当然,这是一个富有隐喻性的故事。故事里的这些人,真正所患的,并不是失眠症,而是孤独症。
三
十月过完,秋天仿佛就在天地间寂灭了,接下来便是冬。最近在文学课上讲到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
那天下午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收到了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电报。那是一次例行公事的谈话,没有为胶着的战局带来任何突破。谈话即将结束时,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望着荒凉的街道、巴旦杏树上凝结的水珠,感觉自己在孤独中迷失了。
“奥雷里亚诺,”他悲伤地敲下发报键,“马孔多在下雨。”
线路上一阵长久的沉默。忽然,机器上跳出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冷漠的电码。
“别犯傻了,赫里内勒多,”电码如是说道,“八月下雨很正常。
在人世间备感孤寂的许多时刻,我们曾学着马尔克斯上校给一个人发电报,被孤独负重的手指打下一行字:马孔多在下雨。祈望他能理解。可对方只是回:八月下雨很正常。
孤独是全人类的慢性病,它并不致命,但足够深入骨髓。但人与人的孤独,彼此并不能真正感同身受。犹如一场雨,共同覆盖着你我,但雨中你我的泪水各不相融。这是生而为人的困境,由一场雨水带来的启示。
雨水是储藏情绪的容器。一个人年轻时总是雨水太多,泛滥成灾成河,后来我们学会收敛雨水,把它们装进各式各样的瓶瓶罐罐。当盖子不被打开的时候,我们甚至忘记了曾经是否为谁而哭过。后来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在滔滔生活中逐渐变得麻木,正常。正常地去接受一切合理与不合理,一切快乐与不快乐,这是一件令人感到可怕的事情。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想,我一定是把太多瓶子封存起来了。
我决定仍旧做个天真的人,留存一些透明的瓶子去盛装雨水。 (摘自《红岩》2024年第6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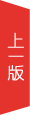



 上一篇
上一篇